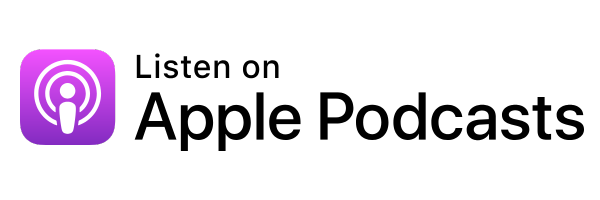杨:我想有些最开始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的人,真诚投入的,后来也因为各样的曲折使得他们有一个思想转变。其实那个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经历,很多人是一直到文革后期才醒悟过来。
王:是的,所以我有一个1949年后的“四场文革”的分析。任不寐和刘军宁也说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场“文革”就是从基督教而起的三自运动,这是镇压反动会道门的一个延续,打击焦点是宗教界。第二场“文革”是对私人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击的是商界和资本家。第三场“文革”是反右运动,打击焦点是知识界。最后才是第四场“文革”,打击焦点是党内当权派。为什么政教关系是第一位的呢?共产党进城之后要巩固他的政权,对他来讲,建国就是一个创世记,所以他们说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政权。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统治形式,政教合一的,身体跟灵魂的,政治、经济、文化被纳入一个整全的世界观的统治形式的出现。阿伦特称之为“极权主义”,或港台翻译的全能政治。这实际上是欧美世界“去基督教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世俗政权本身的神圣化和宗教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第一场文革是针对宗教,尤其是针对基督教会来的。因为他背后的统治合法性,是一个宗教化的乌托邦意识形态。
在1950年后,一些西方差会有所反思,他们意识到,20世纪基督教宣教的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失败,都发生在中国。内地会有一位宣教士,大概在1951年纽约的一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反思。他说,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没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可以周延的让你理解宇宙的来源和生命的价值,理解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断裂的,知识分子得意的时候就是儒家,失意的时候就是道家。这个世界观也是混沌的,含糊不清。如庄子说的,你想要搞清楚,那浑沌就死了。所以,中国人的精神要么是保持在空虚混沌的状态,要么是保持在一种清醒而割裂的状况。知与行之间,是没有办法合一的。个人修行跟政治哲学之间,也全是割裂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模型。因此,这个宣教士说,我们(教会)比共产主义传到中国来,其实早了100多年。我们先来,他们后来。但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教会虽然传福音给中国人,却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一套基于圣经的、完整的世界观。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简单而断裂的。信了福音的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中国人,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巨大的变迁。结果呢,他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接受的第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
这是差会当年走得最远的一个反思,“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反过来说,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拥有完整的世界观的现代极权主义政权。一两次,他需要的不只是政治斗争,他必须把旧世界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他的新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只是暴力革命的胜利,而不是“建国”的完成。“建国”的过程必须同时是一个“文化革命”。所以不是1966年才开始文化革命,1949年后,一个创造新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因为文化革命才是极权主义的实质。而在这场革命中,谁是他的第一个敌人呢?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凯撒与基督之争”。
所以我说,第一场文革是“宗教革命”,镇压所有的宗教。镇反运动,消灭民间宗教,三自运动,消灭外来宗教。不拜凯撒的人,统统都是反革命。只有宗教革命的成功,才能使他确立政教合一(或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说,就是君师合一)的地位。第二场文革是“经济革命”,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基本完成,用共产党的语言,叫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三场文革是“知识革命”,1957年的反右运动,矛头指向旧知识分子,是后来那场文革的预演。所以我常常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自许甚高,以为自己是共产党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总是把宗教排在最后一位,把狭义上的文化排第一位。但他们骨子里其实从来都是把政治排第一位的,千百年来,儒家传统的精髓,就是文化依附政治,士子依附明君。所谓大儒者,三公也。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共产党政权的现代极权主义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中建造一个全能政治的新世界。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看见,新政权的第一个敌人是谁?凯撒非常清楚,他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基督和祂的教会。共产党也非常清楚,他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事实上,虽然知识分子有一个逐渐清醒的过程,从1957年开始,到文革中后期尤其是9.13事件之后。西单民主墙的影响有限,然后直到1989年。但我认为,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中共政权本身的“宗教性质”,从而反思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因此,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包括民间的反对派,仍然与共产党共享着同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