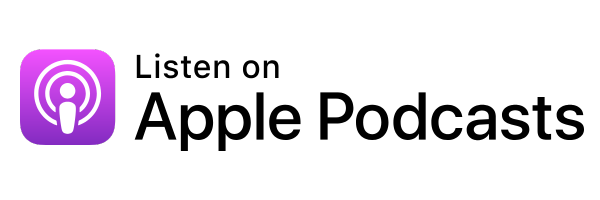世人可能有一样的行为,如施舍一个乞儿。但心思意念却有万端。有一本希腊世界的“诸君王和统帅名言录”,记载了斯巴达统帅布拉西达斯的一件事。他捕到一只老鼠,被它咬了以后,就放掉了它。布拉西达斯认为,“如果这只老鼠确有保卫自己的勇气,它就应该得到自由”。他说,再没有比杀掉它更可鄙的事了。另一位中世纪的修士贝拉尔曼,也曾耐心恭顺地让跳蚤和其他可恶的害虫去咬他,不愿把他们掐死。但他说出的是另一种世界观,“我们有天国可以报偿肉身的苦难,但这些可怜的受造物,除了享受现世的生活之外一无所有”。
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评论说,这就是“一个希腊英雄和一个基督教圣徒的名言的区别”。若不是超出了我写作的界限,也可以再加一段佛教徒的故事和他的世界观,一起观照。
今天的世界,一个人若不是一神论者,多半可能是希腊的传人,或者黑格尔的信徒。自从初代教父特土良说出那句著名的话,“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人心中关于这个世界的场景,就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不断漂移。人心中的楷模,也就在英雄和圣徒之间反复流连。而人渴慕效忠的对象,也从此就在国家与上帝之间见异思迁。
在希腊和希伯来之间,黑格尔断然选择了前者。在他看来,希腊的悲剧英雄,最迷人之处,就是“高贵的人由于命运的支配而陷入必然性的失足”。希伯来的悲剧呢,却是服役的人被他们的神无情地抛弃。克尔凯郭尔的看法与他相反,他嗤笑那些理性主义者看不见信心的伟大。他称希腊英雄是一种“伦理英雄”,而圣经中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先知则是“信心英雄”。不是伦理,不是血气,也不是理性,而是对上帝的信靠,才叫人的一生脱离了偶然性的威胁,而能在一切处境中分沾天国的荣耀。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则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一书的前言,针锋相对地引用了柏拉图和保罗的两句话,好像一论一答,来表达他对理性崇拜和伦理国家的反对。
柏拉图立论,“人的最高幸福莫过于在谈论美德中度日”。
保罗反驳,“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很难否认,《斯巴达勇士(300)》是一部极度风格化的电影。原著弗兰克·米勒黑色漫画的精髓,古典油画的气质,把剧情的一切单薄都厚厚地覆盖了。只是当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从口中吐出“正义”或“自由”时,我就羞得恨不能钻下地去。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曾用尽一切华丽和明亮的词语,来描写撒旦的诱惑和始祖的堕落。甚至整本《圣经》也很难以一个贬义词来形容魔鬼。反而称他是光明的天使、明亮的晨星。“丑恶”,是一个被深深误解的词。“丑”是因为它“恶”,而不是因为它“丑”。从亚当的堕落开始,真正的恶常常都以美的形式出现;真正的诱惑,也首先是审美的诱惑。米勒说,他 6 岁时和父亲一起去看 1962 年版的《斯巴达三百壮士》,受到极大震撼。斯巴达战士的头盔和红披风,在温泉关前,以 300 人抗击 10 万大军(有说 30 万或 100 万)。斯巴达人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一种没有保质期的英雄主义。一个男孩,有可能不被诱惑吗?可惜米勒长大之后,这个世界的审美观几乎只剩下了一个字,“酷”。酷到死,酷到肉体的极致。连一个 60 岁的美国老太太从影院出来,回答记者,也是这个字,“太酷了”。
我又重看了 1962 年的版本。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的斯巴达,被描写为希腊文明的守护者。面对波斯帝国的进犯,斯巴达与雅典的差异被有意淡化了。捍卫家园和信守诺言,是国王列奥尼达的两个勇气来源。于是 300 壮士背靠希腊,在关前的豪迈就被政治正确化。画外音甚至点出,希腊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自由世界。温泉关上,正是抵御东方专制主义的前线。换句话说,温泉关就是柏林墙。
而冷战之后,好莱坞将如何重述一个温泉关的故事呢?导演也忠实于米勒的原著,把 300 壮士的故事,从希波战争的思想史背景中抽离出来。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只去渲染一种创始成终的血气,连电影名称也只剩一个干脆的数字。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打破了老版本中的统一战线,把斯巴达与雅典的迥异完全显露出来了。让你知道,一旦打败波斯,雅典和斯巴达的内战就不可避免。就像希特勒一被摧毁,才发现盟军里面,既有丘吉尔,也有斯大林。
影片中,每一个被扔进山谷的斯巴达婴孩,每一个在丛林原则下被一路淘汰的斯巴达少年,又叫你发现原来“以少胜多”也是一个假象。什么样的社会,可以煅炼出抗击 10 万大军的 300 勇士呢。要在敌人没来之前,就去芜存菁,先把自己的孩子杀掉一半。你恍然大悟,原来这不过是人海战术的另外一种。波斯的人海战术,是把奴隶们开到战场上当炮灰。斯巴达呢,是上场之前就替对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也是柏拉图在《王制》篇中,曾经忧心忡忡的问题。斯巴达是希腊文化的一股暗流,甚至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国家主义的一种主流。就是以血气捍卫城邦的正义。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理性”可以概括的。雅典和斯巴达,代表着希腊世界的两极,即“血气”和“理性”。人们凭着血气,去守卫自己的“应得之物”,从而“在人类事务中维持着一种微弱的稳定性”。这就是希腊。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叫“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说这话的人组织起来,曾经自称为“斯巴达团”。
于是柏拉图提出他的疑问,“如果战士严酷而残暴的对待城邦的敌人,那么他们会不会也这样对待城邦的公民呢”?
答案荒谬但是肯定,恰恰只有先对自己的公民“秋风扫落叶”,才能对自己的敌人“秋风扫落叶”。柏拉图继续他的思考,问血气和温柔是否可能在一个城邦中完美地统一?他发现,自然界中这两种天性能够共存的唯一例子,就是狗。国家不能是狮子,不然公民就受到威胁。国家也不能是兔子,不然容易被外敌倾覆。那么国家就只能是一条狗,对外敌凶狠,对公民摇尾巴。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一只狗就是“哲学狗”。他提出一条在政治中节制血气的道路,就是哲学与血气的联盟。国家只能由“哲学狗”(或哲人王)来领导,就像在希波战争中那样,雅典人的智慧,加斯巴达的血气。这就是 1962 年版本的格局。而在《300》中,列奥尼达这头狮子是怎样嘲笑那只哲学狗的呢。他说,如果连那些哲学家和恋童癖都有勇气拒绝薛西斯,何况我们斯巴达。说罢一脚就把波斯使者踹下井去了。其实这话至少有一半美化了斯巴达。哲学对他们来说固然难了些,但当时同性恋的风气弥漫整个希腊,也包括斯巴达的军营。
无论斯巴达的君主议会制,还是雅典的公民民主制,无论自由的希腊还是专制的波斯。城邦或国家的荣耀都大过了一切荣耀。无论君主、僭主还是“哲学狗”,都渴望在伦理国家之内建立一个至高的,让人把生命委身于它的主权。别尔嘉耶夫在探讨人的奴役时说,“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的诱惑”。人在历史中,不断寻求自己的王国,终其一生去建立它,施行统治。这就是凯撒那句名言的意思。“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这一场希波战争,与曾发生在迦南地的那些争战不同,在以色列人那里,一个“民族国家”从来不是争战的目标。但在这里,征战双方都将一个虚妄的主权看作世上绝对的偶像。300 也好,10 万也好,无论我们身在哪个阵营,我们都是国家之下的奴隶。我们对一个更高的国度失去了想象力,甚至也失去委身的渴望。当列奥尼达这个从小以杀戮求生的人,说出“自由”一词,当他的王后说“要不带着这面盾牌,要不躺在上面回来”。我真的毛骨悚然,想起日本母亲在儿子出征前的“祈战死”。也想起一位诗人在狱中的哀号,“祖国啊,你这嫁不出去的东西”。
卡西尔批判的“国家的神话”,本质上是一个主权的神话。借着这一神话,国家成为历史的暴发户。奥古斯丁说得更坚决,所谓国家就是罪恶与魔鬼的一件作品。别尔嘉耶夫则指出,人类史上能够拒斥“王国”神话的,只有旷野试探中的耶稣。福音书记载,撒旦三次以世上的权柄试探饥渴中的耶稣,耶稣却三次引用《旧约·申命记》的经文斥退了撒旦。
当魔鬼说俯伏在我脚下吧,我就将世上的万国和一切荣华赐给你。从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到罗马,从亚历山大、凯撒到拿破仑,从彼得大帝、希特勒,到列宁和斯大林们,无数的君王都在地下痛哭。当初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电影中,那个幽灵一般的薛西斯也向列奥尼达提出类似的诱惑,投降吧,我把整个欧洲都送给你的勇士们。在世俗的和属灵的两个国度之间,耶稣以十字架拒绝了撒旦。以受膏者的血,划出一道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停火线,“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而在地上的东方与欧洲两个世界之间,列奥尼达也凭着他狮子般的血气,回绝了薛西斯。最后以一个十字架的姿势,死在乱箭之下。
希腊是一个没有确据的世界,连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都在与命运搏斗。温泉关之战,是人与历史的一场搏斗。斯巴达人的血固然值得尊敬,但吊诡的是,这一场搏斗却形成了历史崇拜的一部分。勇士的骸骨不能复活,却成就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偶像崇拜的神话。休谟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布拉西达斯,以羡慕的口气说,“在希腊世界,所有城邦和殖民地的创建者都被人们推举到一个仅次于神的等级”。他也和黑格尔一样,认为只有诸神之争才能激发历史的活力。各种偶像在人心中此起彼伏,争夺着奥林匹斯山上那个最高的宝座。
在雅典,曾有个叫斯提尔波的人,被他们的最高法院放逐。因为他宣称城里的密涅瓦不是一尊神,只是雕塑家菲迪亚斯手上的一件活路。而在罗马附近的狄安娜神庙,任何一个杀死祭司的人,都有合法的资格继承死者的职分,担任祭司。
这就是诸神之争,就是这两千年的历史。甚至当欧洲人成为基督徒以后,雅典和斯巴达仍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联手辖制着他们的后裔。构成了一个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称之为的“黑暗王国”。一个“罗马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一神胜过了诸神,信仰却难以胜过文化。霍布斯引用耶稣的比喻说,“但谁又能说那些被赶走的污鬼将来不会回来,甚至带回一群比自己更恶的鬼来,进到这打扫干净的屋子里并住在这里,使这儿最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呢”。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学和国家学说,当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城邦主义在欧洲全面复兴以后,他的预言也成了现实。无数变种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使“国家”重新成为旧约里的怪兽“利维坦”。
别尔嘉耶夫在评论法国 19 世纪末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时,他说,“一个仅次于神的国家,具有一种魔鬼般的诱惑”。这个国家忍不住一次次把他的公民送上断头台,使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的声音在时间以内回响不绝。只要能增进法兰西国家和军队的利益,别尔嘉耶夫说,你看吧,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处死一个无辜的人。
地上的万国就像诸神,明明高不过历史,偏要一心把自己举过头顶。冷战结束了,文化的纠葛却永不停歇。今天的伊朗以波斯帝国的继承人自居,这部电影刚一公映,他们的总统顾问就抗议,指责好莱坞妖魔化了波斯文化,意图涂抹历史,好为美国的反恐战争造势。对这种事,我常常缺乏评价能力。我不知道怀念斯巴达做什么,怀念柏拉图那只政教合一的哲学狗做什么。我 10 岁的时候,和好朋友孔文一起去食堂,背一大桶酸辣汤回教室。路上有一只显然缺乏哲学修养的看家狗,冲过来咬了我的大腿。直到十几年后的新婚之夜,我的瘢痕终于才彻底消退。这辈子我一看见狗,就心中发怵;一听见狗叫,就慌了阵仗。我常常沮丧,为什么被一只具体的狗咬过,这么难克服心中的畏惧。而被一只抽象的狗咬过的人,那么快就容易淡忘呢。
妻子说,假设你被拷问,只要牵一只狗来,你就完了。我考虑良久,还是决定把这个软肋写出来。有许多英雄故事,仿佛是为了预防人们的偶像崇拜,英雄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如阿喀琉斯的脚踝和参孙的头发。又如练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大侠,身上必有一个功力不逮的罩门,一碰就完蛋。何况我们这些小子们呢。知道了自己的脆弱,就知道“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就如使徒保罗的软肋,是他肉体中的一根刺。但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说,这样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人若如此,人的国家又如何?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