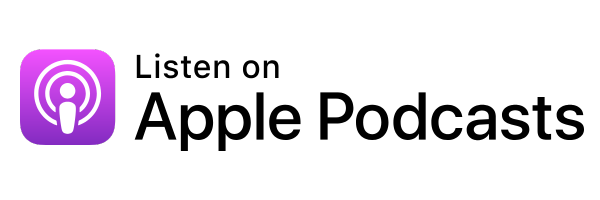1
唯有将外表和内心结合起来才能认识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亲身领餐、亲身下跪、亲耳读经、亲口祈祷。把灵魂的救赎寄托于仪式,这就是迷信。然而不肯让身体顺从于仪式,这就是高傲。基督教将卑微的人提升到内心,将高傲的人降低到外表。缺乏任何一面就不是真信仰。
2
人们以为,言必称上帝的人是危险的,那是因为人们不认识上帝,只认识那个人。事实上,在谈论任何庄严和重要的事情时,绝口不提上帝的人,才是危险的。因为这等于公开声明,他们拥有无限责任能力;或预先宣称,当他们宣誓、求婚、上诉和写微博的时候,谁若过于当真,谁就是瓜娃子。
3
跛脚的人不会令我们生气,跛脚的思想却会激怒我们。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直,跛脚的思想却咬定我们才是跛脚的。我们生气,因为我们对自己是否跟随了真理并不那么有把握,尤其当我们的信仰被很多人讥笑时。强迫人的身体,你必须诉诸刀剑。强迫人的灵魂,你只要诉诸他的怀疑。
4
帕斯卡尔批评蒙田,说我们可以原谅启蒙作家有点自由而又放荡的感性,却不能原谅他们“纯属异教的对死的情感”。当他们谈到死时,都是优柔怯懦的,“既不畏惧也不悔改”。在所谓的启蒙精神中,对死的虔信的焦虑已经死了。换言之,他们谋杀了一个古典时代,这是何等恶劣的骗粉行为。
5
帕斯卡尔说,有关外物的科学,不会在我痛苦时安慰我在道德上的愚昧无知。有关道德的训诫,却永远可以安慰我对外物科学的愚昧无知。我们可以教人一切,却不会把人教成正直的人。夸耀自己懂得任何事物,都不如夸耀自己的正直。但我们却永远无法夸耀、自己根本不曾拥有的东西。
6
自爱是可怕和勉强的,自爱无法防止他所爱的对象不充满错误和悲哀。自爱在人身上产生了一种最令人发指的情感,就是对那个谴责他、向他的良心作证他的缺陷和罪过的真理,怀着一种要命的仇恨。就像杀人犯清理现场一样,人类创造文化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真理的光明。
7
人的情感总是跑在意志的前面。如孩子们用眼泪控制他们的母亲,我们也习惯于用 I Wish来替代 ISwear。于是我们常在信仰上成功的欺骗自己。就如帕斯卡尔所说,“人的心一旦想到了皈依,就自以为已经皈依了”。就如一旦想到奉献,就不需要再奉献;一旦想到爱,就已忍不住流下泪来。
8
人不外是一个充满着错误的主体,假如没有神的恩典,这些错误就自然而然又无可避免。我们的理性和感官,都缺乏真诚,并彼此欺骗。感官以虚假的表象欺弄理性,理性以推理的骗局,反过来对感官进行报复。就像两根互相撒谎的筷子,夹不起圆满的人生。
9
想象,是人生最具有欺骗性的部分。一位理性的敌人,一种高傲和狂幻的力量,没有它的批准,一切财富、美和幸福都不合法。它倾向于将微小的对象一直膨胀到充满整个宇宙,如我们谈论自己的时候;又以粗鲁的方式将宏伟的事物一直缩小到它自己的尺寸之内,如我们谈论上帝的时候。
10
我们骄傲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很愿意在一次伟大的苦难中牺牲自己,只要死亡能够换来人们的谈论和敬意;假如还换来了一位女性的眼泪,甚至行善也不是很艰难的事。因为我们做梦都希望别人为我们的不朽而流泪,但唯有基督这样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哭”。
11
基督并没有医治我最痛恨的疾病——无助和无能,基督反而成为无助和无能的样式,使天国的大门惟独向着无助和无能的人敞开。有人轻蔑地问,基督教不就是弱者的精神安慰吗。我说,你说得对。基督教意味着,一切强者都与天国无分。
12
我爱贫穷,因为上帝爱贫穷。我爱财富,因为财富提供了帮助不幸者的手段。我力求对一切人怀着忠诚,但对上帝使我与之格外紧密结合的那些人,我怀着由衷的亲切之情。我天天感恩我的救主,他以恩典的力量,把公正、真实、诚恳和忠心,安置在一个充满了脆弱、可悲、欲念、骄傲和野心的人身上。
13
没有耶稣基督,世界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那必然是要么世界终将毁灭,要么世界活像一座地狱。理想主义者描绘人间天堂,现实主义者抱怨人间地狱,基督徒却只传扬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14
帕斯卡尔说,人是配不上神的,但他并不是不可能被转化为配得上神的。神把自己与卑污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是配不上神的,但神把人从卑污之中救赎出来,这却不是配不上神的。人类的思想,要么认为人神之间无限遥远,要么认为人神之间有奥秘的感应。但圣经却将一切的奥秘和荣耀,单单归给了基督。
15
凡是在信仰上不把上帝当做一切事物的原则来崇拜,在道德上不把唯一的上帝当做一切事物的目的来热爱,这样的宗教便是虚妄的。正如一位清教徒牧师所说,在彻底的加尔文主义和无神论之间,没有任何稳妥的立脚点。因此,帕斯卡尔说,反对那些漫不经心地相信上帝的仁慈、却又不肯脱离罪恶的人。
16
有一个人,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在监他的行为,但不得不相信有一个政府几乎能监视他的一切行为。不相信有一位基督为他的罪流血,但不得不承认这世界每天都在为罪流血。不相信有一位圣灵掌管他的心,但难以割舍每天的广告、新闻、微博,每张美女图片,都在抚摸和争夺他的心神。曾经,我就是这个人。
17
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能复活?哪一个更困难,是降生,还是复活?是未曾有过的要有,还是曾经有过的要再有?重现,难道比出现更神奇吗。猴子变成人,难道比水变成酒更容易吗?宇宙从无中生有,难道不比童女怀孕生子更令人难以置信吗?万有引力,难道不比上帝的护理更神秘、更像一种魔法吗?
18
悲哀的不是死,悲哀的是怕死和对死一无所知。可耻的不是活在黑暗中,可耻的是根本不相信光明。怯懦的不是眼泪和屈膝,怯懦的是作反对上帝的勇士。
19
上帝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可悲。这意味着只有认识到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才认识了上帝。以及,只有在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时,才能认识作为拯救者的上帝。因此,那些不认识自己的可悲就认识了上帝的人们,并没有使上帝显得更高超,而只是使他们自己显得更高超。
20
灵魂的全部安慰都在基督里,灵魂除了爱上帝以外就没有別的欢乐。看见山川秀美,使眼目清爽,看见天高云淡,使身心通泰,但若不将敬畏惊颂归给造物的上帝,灵魂就没有快乐。人约黃昏,执子之手,使情意荡漾,血气方刚,但若没有天长地久的不朽盼望,灵魂就没有快乐。
21
帕斯卡尔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对上帝的形而上的证明,即不要耶稣基督而得出的对上帝的认识,或一切不能使人认罪人的知识,都是徒劳的。如奥古斯丁所说,“他们由于好奇而认识的,又由于骄傲而丧失了”。
22
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便形成骄傲。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上帝,便形成绝望。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其中既认识上帝、又认识我们的可悲。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我们与他接近而不会骄傲、我们向他屈卑而不会绝望的上帝。
23
一些哲学家鼓舞纯粹伟大的情感,另一些哲学家鼓舞纯粹卑贱的情感,但这两种都不是人类的状态。卑贱是必须的,但不是出于人性而是出于悔改,不是为了停滞其间,而是为了步入伟大。伟大也是必须的,但不是出自优异而是出于神恩,并且是在经历了卑贱之后。
24
祈求是不在人类权力以内的要求。请愿是在人类权力以内的要求。人当向上帝祈求,向政府请愿。向神请愿为叛乱,向人祈求为下贱。上帝将祈求赐给无权祈求的人。除了被允诺的儿女外,他不曾允诺过任何祈求。祈求意味着人类依靠无权获得的恩典而存活。地狱不是不祈祷,地狱是充满一厢情愿的祈祷。
25
基督徒在最细微的事上也依据信仰行事。大海会因一块石头而起变化。在神恩中,最细微的行为也会以其后果而关系着一切。因此一切都是重要的。愿上帝不要把我们的罪咎归于我们,也就是别追究我们罪恶的一切影响和后果;其中哪怕最细微的过错,假如我们无情地追究到底的话,也都是非常可怕的。
26
上帝对人们的一生所进行的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不让他们经受这场战争。好像一个母亲从强盗手里夺回自己的孩子,我们当憎恨那不公义的拘禁了他的凶恶专横的暴力,而爱母亲为他取得自由的深情而合法的暴力。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路12:49)。在此之前,世界生活在虚假的和平中。
27
上帝创造万物,但万物不能感到自身存在的幸福。于是上帝创造人,能认识上帝,又能构成一个能思想的整体的生命。有彼此结合的幸福,可惊叹的智力的幸福,在万物中成长和延续的被眷顾的幸福,有善意可以响应那至高的善的幸福。人若藐视和背叛这些幸福,与其说是爱自己倒不如说是恨自己。
28
斯巴达人的慷慨赴死很难打动我们,因为那不能带给我们什么。但殉道者的付出却打动了我们,因他们是“我们的肢体”(罗马书12:5)。我们和他们有一条共同的纽带,他们的坚决可以构成我们的坚决。就像我们看见一个官僚富有,并不会感到自己富有,但看见父亲或丈夫富有,我们却感到同等富有。
29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一个民族出埃及之前,这是庄严沉郁的主旋律。亚伯兰的父亲带着全家出吾珥,去迦南,途中死在了哈兰(创11章)。之后,亚伯兰听到耶和华上帝的呼召,继续出哈兰,去迦南(创12章)。看上去,父子两代的路线是一样的,实质却不同。一个是移民计划,一个是天路历程。——写在余杰去国之际
30
让我们想象一个身躯充满了能思想的肢体吧。让我们仅仅爱上帝并且仅仅恨自己。假如脚只具有对于自己的知识和爱,他就丧失了作为肢体的高贵品质。他当以怎样的顺服让自己听命于那个统御身体的意志啊,直到同意必要时把自己砍掉。
31
真正的信仰,是在那位被我们不断激怒、并可以随时合法毁灭我们的普遍的存在者面前否定我们自己;是承认除了他的羞辱和咒诅外我们就配不上他的另眼相看;是看见上帝与我们之间有不可克服的对立,若没有一位中间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交通。事实上,除了信仰,你能够期待的唯一的奇迹就是末日审判。
32
帕斯卡尔说,“反对只要上帝而不要耶稣基督的那种哲学家”。他们将上帝下降为一位精准的钟表匠的上帝,或一位心中的道德律的上帝,或第一推动力的上帝,或逻辑起点的上帝,或一位为人民服务的上帝。他们并没有以他们的思想取消罪恶,“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以骄傲为基础来运用罪恶罢了”。
33
人人都是天然彼此为仇的。我们尽可能地运用欲念,使它为公共福利服务。但这只不过是伪装,是仁爱的假象。怜悯不幸的人并不违背我们的欲念,相反,我们可以很容易拿出这种友好的证据来获得温厚的名声,而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出于欲念的善行,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仇恨。
34
承认原罪是愚蠢的,但这种愚蠢要比人类的全部智慧都更有智慧。否认原罪是邪恶的,这种恶在今世诱惑人,在来世则控告他。#创世记#8章21节记载,上帝对挪亚说,人从幼时心就是恶的,但上帝却与挪亚立约,存留宇宙的秩序,不再为人的缘故毁灭这地。承认原罪,就是跪下来,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
35
距离人类知识最遥远的神秘,就是关于罪的传递的神秘。没有什么比原罪更能震撼我们的理智,或更粗暴地触犯我们自己可怜的正义准则。然而,人生一切境况的症候都在这一深渊里回环曲折,以至于理智的高傲的活动,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若没有对这一最不可理解之神秘的理喻,我们对自己就不可理喻。
36
帕斯卡尔说,人是宇宙的光荣兼垃圾。我们既有对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我们既不是绝对无知,而又不可能确实知道;我们曾身处一种完美世界,而又不幸地从其中堕落。没有任何别的宗教曾认识到,人是一切被造物中最尊贵的,而又是最卑污的。
37
人若不确定自己站在上帝面前,人就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所以怀疑主义倒有最起码的诚实。人若不能确信自己看见了真理,人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所以悲观主义,倒比一切道德主义更有道德。人若不绝望,你向他传什么福音呢;人若不怀疑自己的怀疑,你向他谈什么信仰呢。
38
“如果你们与上帝合一,乃是出于神恩,而不是出于天性。如果你们屈卑,乃是出于忏悔,而不是出于天性”。球已经落在半空,谁能使它回到起点呢。野驴已经发情,谁能使它安静呢。我已转身离开了你,谁能使我们面对面呢。
39
可怜的亚当,你已不是当初被造的样子。你的全部知识已经熄灭。对你俯首听命的万物都起来反对你,你的身体也是潜伏的仇敌。这世上的一切不是刺痛你,就是诱惑你;不是凭其力量使你屈服,就是以其甜蜜使你沉湎;从而统治了你,这是格外可怕又格外暴戾的一种统治。事实上,这就是专制主义。
40
什么是爱一个人呢。如果他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直到他理解到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直到他发现,爱就是像爱一个王子那样去爱一个怪物;直到他因徒劳无功的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感到疲惫,从而向人类的救主伸出手去。
41
关于上帝:我们对于证明,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是一切理性主义者所无法克服的。我们对于真理,又具有一种信念,这是一切怀疑主义者所无法克服的。
42
恶是容易的,数目无限之多。善却是独一无二的。如蒙田说,千百条道路都错过了洁白。但有一种恶几乎和善一样难以发现。故此,人们往往把这种特殊的恶当作善。简直只有少数超凡伟大的英雄和圣人,才能企及那种人迹罕至的恶(帕斯卡尔)。这种恶的特征,是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得荣耀(马丁路德)。
43
如果我们每夜都梦见同一件事?一个匠人每晚必有12个小时梦见自己是国王,那么,他大概就像每晚必有12个小时梦想自己是匠人的国王一样幸福。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梦是不可把握的残片。不信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梦,信的人每天都有相同的梦。没有同一位上帝,哪来同一个梦想?
44
太年轻,难以断定世事,太年老也是如此。想得太少,容易出错,想得太多也是如此。站得太近,难以欣赏一幅画,站得太远也是如此。只有一个点是完美的,其余的时间、距离、年龄或主义都不靠谱。在绘画上,透视学规定了这样一个点。但在真理上、道德上,有谁来规定这样一个点呢?
45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人们不惊讶于自己的脆弱和无知。很少有人在谦卑地谈论着谦卑,很少有人在圣洁地谈论着圣洁。也很少有人在怀疑中谈论着怀疑主义。我们不过是谎言、歧义和矛盾中的浑水摸鱼者,我们藉一切的谈论,向自己隐瞒了自己,向别人打扮了自己,也向上帝暴露了自己。
46
微博,偶然引起了思想,偶然也勾销了思想。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但当我要写下自己的思想时,它却逃逸了,这使我记起了自己的脆弱。思想何等伟大,思想又何等卑贱。这个事实所教导我的,并不亚于我那被遗忘了的思想。因我并不祈求认识自己的丰富,我只祈求认识自己的虚无。
47
一件并不可耻的事,一旦受到群众赞扬,就难免成为可耻的了(西塞罗《论至善》)。人的善行承受不住赞扬,就像会思想的芦苇承受不住雨水。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承受不住被囚禁的妻子的眼泪。我们对得起这个人,就对不起那个人。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十字架上没有复活。
48
人最好的德行也包含着罪恶,如解药包含着毒药。情感往往产生自己的对立物,吝啬有时产生挥霍,嫉妒有时产生热爱,由于脆弱我们坚强,由于怯懦我们勇敢,由于自卑我们坚定。我们保持了德行,只是因为两种相反的罪恶,就像在两股相反的飓风中直立行走,一旦克服了一种罪,就会倾向于另一种。
——摘自《大声的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