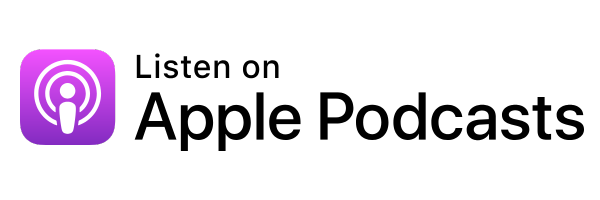非洲菊和白玫瑰: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我选了这两种鲜花,追思告别后,跟家人一起,和岳父的骨灰一道,撒在一段江面。
恰好是我和妻子初恋常去的那一段。筑坝之后,江面拓宽,原先我们坐在那里的草地,已不见了。吻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在那时写下诗句,
“吻你时我发现人类的无力/梦想上帝把你还原为我的肋骨/当初亚当和夏娃是如何离开的/那个晚上。我们像领取圣餐一样开始接吻/并在内心坚信,我们的子孙/终将回到赤身露体的园子”。
那样的年龄,怎能想到,生有时,死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岳父的骨灰,十几年后,也将从不远的水面漂走。人类筑坝的动机,也不过是想挽留更多的东西。在宽阔的水岸,我们像富足得不肯松手的人,却终将有限的身体,投入流动的江河。江河能去哪里?《传道书》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譬喻,人归了他永远的家;尘土仍归于尘土,就像江河仍归于江河。但灵魂,却归于赐灵魂的上帝。
所以,撒去骨灰,不是对生命归宿的一种确信,是对循环往复的一种文学性的处理手法。同一天,我收到廖弟兄娃儿降生的短信。早上醒来,端过儿子的脸,在晨光之下,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彷佛仅仅是属于这一天的。我以往未曾见过,我对小书亚说,送走了外公,你就长大了。
一周前,收到艾晓明制作完成的这部纪录片。关于地震中失去的娃娃,看过不少民间流传的影像。但这份记录,沉甸甸的,又将我带回512后的那半年,渐渐听见上帝对我传道的呼召。
教师,是一份在死亡面前无法自持的职业,就像儿子是一个在父亲死亡时无法自持的名分。13年前,我在大学任班主任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女生,班上的学生委员,怪不好意思的,提着一盒月饼来我宿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月饼。多年之后,我遇见一个学生,告诉我,那个女孩因为恋爱,遭家里反对,就悬梁自杀了。
那个晚上,我哭了很久,因为忽然意识到,她之所以送我月饼,和她自杀一样,都是不情愿的。只是其中绝望的程度不同罢了。倘若我所言所行,都要影响人的灵魂,那么教师就像法官、祭司或君王,根本就不是人可以干的。谁能穿上那身衣服,谁能登上那个宝座,谁能站在那个讲台呢。
如果人有灵魂,我怎敢做人家的教师,我也不敢做人家的儿子。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无法将那个女孩的死,和我作为她老师的身份在因果律上彻底撇清,也无法将我与我亲人的死做个了结。许多人都有自怨,说自己倘若如何,他(她)就不会死了。心理学在这一层面都是自欺欺人的。逻辑上说,只有两种情形,可以撇清你与他人死亡的干系。其一,世上万事都是一个绝对的偶然,因为秩序的缺乏,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其二,有一位上帝,在他绝对的旨意中成就万事,各按其时。
意思是,第一种情形下,你的悔恨全无用处;第二种情形下,你在悔恨之上能够选择信靠。两种之间呢,是我明明看见了某种因果,却无法相信更高的原因。这等于把我的作为,摆在了一个至高的、被问责的地位。我的良心,如何可以承受煎熬,卸下重负?
一个教师不相信上帝,他一开口,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做真理的代言人。一个政府不相信上帝,他一动粗,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作了权力的图腾。我看了这片子,忍不住将离世的岳父,和垮塌校舍下的娃娃做个对比。尽管亲疏有别,我的伤痛,仍难分轩轾。不过地震若非在四川,对台湾风灾的罹难者,我就淡漠得多。一周前为灾区的祷告会,我心口子痛,想起一年前的委身,惟愿大地的余震,永远在我灵魂深处不断绝。如今的安逸,彷佛8万人都白白死了。孩子们的死,若没有迟到的公义,怨恨的力量,就大过地震波,仍在灾区蔓延,直至人心深处。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最好的心理辅导,就是公共责任的追究,与真相之上的忏悔。不然,每天做三次深呼吸,躺在治疗床上倾诉一小时,于人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
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永远伴随着对人的追问,而非对遗忘与虚谎的宽待。还有差别,岳父经过一生,死于癌症,他的死是家事。娃娃们殁于天灾,又纠结于人祸,他们的死是天下事。
但奇怪的一点,尽管死于校舍垮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给了人们最大的道义感染力。独生子女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中,也有着极昂贵的地位。但一年来,这仍未能成为一个极具重要性与延伸空间的公共事件。就像毒奶粉事件那样,慢慢就从天下事退回了家事。
说到底,中国人的灵魂观是建立在惧怕之上的。鬼神也放在一起说。许多出租司机不愿到殡仪馆;尽管机会都一样,人们通常也是参加婚礼的多,参加葬礼的少。一个小妹妹说,这里好恐怖,害得小书亚把这新词汇念叨了几天。我在想,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私人情感与公共领域的错位。譬如从人情世故说,父母失去未成年儿女,哀伤程度通常都大于成年儿女失去父母。但儒家传统的“五服”,却不根据私人情感来论定,它非要把失去父母的哀伤拔高,把失去子女的哀伤降低。
这是在背后,把对灵魂之结局的畏惧,当作了治理的起点。王充在《论衡》中,倒很尖锐的指责孔子。他说孔子其实不真信死后有鬼。但祭祀礼仪的目的,是为了威胁臣子。假如不祭祖,说人死如灯灭,乱臣贼子就多起来了。人们公开流露的哀伤,区分为不同规格,这种风气于今仍盛。所以校舍垮塌事件的实质,是家长们的集体哀伤打破了这种潜规则,危害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充说,所以“圣人惧开不孝之源”。向上的维度,装神弄鬼是必须的。向下的维度,就难免冰冷了。
我们的娃娃,在家长那里等于一切,在公共政治上等于零。如同孔子一样,掌权者并不真信人有灵魂。他们的手法和民间宗教的祭祀差不多。就像一个长辈特别嘱咐孩子们,送骨灰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望。
我们对吓得半死的小侄女说,爷爷以前是无神论,现在相信上帝,不相信鬼。你若知道人的灵魂要去哪里,你就不怕人家装神弄鬼。
2009-10-20,完稿后一分钟,凌晨0:44,
北川和平武交界处(北纬32度,东经104.5度)再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千米,在成都写字台摇动,震感强烈。
苦难来得正是时候:《好雨时节》
清明又至。上坟、扫墓的,并不都是无神论者。道场法事,追思礼拜,人们向死而生,也是一个灵魂,各自表述。小时候,戴红领巾,扫烈士陵园。才知道少先队也有祭拜仪式。我悄悄问亲爱的伙伴,为什么团委书记也搞迷信?他是大队辅导员的身边红人。很得意地说,这是文件规定的。从此,我心头有了羞耻感,在烈士墓前,暗暗将袖子上中队长的两道杠,解下来放到兜里。
有个传道人,讲他上山下乡,怎么回了成都。毛泽东去世,乡里开追悼会。事后,问巨幅画像怎么处理?他就说,周总理都是火化,撒到海里。哥几个就怂着乡长,迈开行军步,把主席像烧了。第二天看报纸,他又去恐吓乡长,说这下完了,毛主席是不能烧的,要在水晶棺里躺一万年。几个人嚷着去告发。乡长吓得半死。没多久,他们几个就优先回城了。
这都是老成都的事。几十年来,一些人从过去剥离出来,活成另一群人。一些人还在记忆里斗争,一些人删除了记忆。就像有人是身体移民,精神还在档案里。有人是灵魂移民,身体还在现场。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真实的信仰者,本质上都是“外国宣教士”。因为信仰者的意思,就是在彼岸有花名册,在此岸是寄居者。
人的身份认知,也和信仰有关。在广州,我问一些买房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广州人?他们摇头,说打心眼里,没当自己是广州人。我说是,在成都住了18年,一直就不认为我是成都人。全国3亿城市居民,到底有多少人,愿把自己的命和一座城挂起钩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一座城市信誓旦旦,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样看,钉子户是多么珍贵的财富。没有钉子户,就没有城市文明。因为我们是随时可以撤退的。随时可以换座城市,就像换座监狱。只有钉子户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一个社区真正的委身者,他们热爱和忠诚于政府发放的产权证。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叫那些有任期的空降部队望尘莫及。
但财产或能立身,不能安命。尽管在司法上,不动产决定管辖权,是从民法到宪法,一以贯之的准则。许多导演到一座城市拍戏,也爱说,这是我来了就不想走的“第二故乡”。只是这种轻浮的言语,对钉子户们的伤害,更甚于拆迁。就像老夫老妻通奸,对每一对新婚夫妻的盟约,都是不要脸的拆台。
我是后来才明白,当初结婚,妈妈特别找了骆阿姨,给我们铺床单。因为她婚姻美满,一面贤惠、忍耐,一面还有欢喜。就像画家凡·高,一生反复引用的那句《圣经》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所以偷情的人,若不悔改,就不要出现在别人的婚礼上。掌权的人,若不委身给一座城市,就不要去拆这座城市的房子。
对我来说,是那一天,2008年5月12日。18年的成都户口,这之后,我才真当自己是成都人。我对我的神,重申了人生的“五个一工程”,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个呼召,和一座城市。我在那个夜晚许愿,从此一生住在这座城市,服侍这座城市。
集锦片《成都,我爱你》,是陈果、崔健和韩国的许秦豪,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杜撰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个成都故事。崔健那段过于离谱,陈果拍1976年那段,很有四川的鬼气。许秦豪拍了一段倾城之恋。他单独拿出来发行,取名《好雨时节》。
大地震一周年的前两天,韩国人东河在杜甫草堂,遇见留学美国时暗恋过的女同学吴月(May)。这名字显然是受灾者群体的隐喻。他们若即若离的恋爱,开头像一场偷情。因为双方的婚姻状况,故意留白,不作交待。台词往来,也充满一种韩式爱情片的挑逗意味。直到机场宾馆,吴月在激情中忧伤,止住了两人的亲密。剧情这才层层扭转。原来吴月的丈夫死于地震,她在周年祭前夕,遇见曾经的恋人。行走在伤痛、怀念、迷乱与负罪感中。
大地震的场景很少。电影风格也过于小资化、广告化。但许秦豪的风格,是一贯注于孤零零的二人世界,在这部命题作文中却有突破。他说,如春雨一般,爱情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爱情在他作品中,第一次扮演了医治与安慰的功用。爱情在这里,即是个体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灵魂的。
像“自行车”是个细致的设计。大地震当日吴月骑着车。作为一种创伤转移,她的大脑删除了自己骑车的记忆和能力。东河找到和她以前一起骑车露营的照片,这是吴月第一次被医治,她赶到机场,开始对爱情有了期待。片末,东河从韩国寄回一辆折叠单车。吴月在同事帮助下,骑上车,在杜甫草堂的阳光下微笑。这是全片最动人的画面。我想,凡在那天以后,真知道自己是成都人和四川人的,会为这个画面落泪。
最后,东河站在草堂门口,等着吴月推车,迈过古老的门槛。就像两年了,数百万志愿者站在我们身边,一起迈过门槛。如果好雨知时节,那么地震呢?如果爱情来得正是时候,那么苦难呢。丧父、丧子,丧妻,每个人都要经历。如果一生参加别人婚礼的次数,多过参加别人葬礼的次数,我们的生命就过于委琐。因为不能分享死亡,分享生命就是假的。不能分享亲人的追思,分享他人的喜事就是装的。不能分享灵魂,分享身体就是脏的。
公车上写着,“因为有你,成都更美丽”。我认为,说这话应当沉重而庄严。是的,因为有埋在废墟的孩子,有自焚的阿姨;有天伦之乐,也有孤儿寡母;有妇产医院,也有殡馆墓地;有地震,也有春雨;有警察,也有教堂——
所以电影拍得一般,但我不看不行,不写也不行。感谢朋友阿信,终于完成了他的灾区志愿者访谈录。王兰和吕康银,都是地震中截肢瘫痪的伤员。有个姐妹,一年炖了52只鸡给他们。春节前他们接受了洗礼。还有仁增姊妹,我为她祷告,她流泪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就是吴月。没有韩国来的情人,但有天上来的彩虹。我知道他们对这世界仍有话可说,因为他们失去腿脚,却相信恩典。
2010-3-23写于复活节曁清明节前。
摇啊,摇回家
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记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的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被医治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但如何是安息呢。200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 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之为一个社会。
30年前,站起来的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30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要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23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他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一些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国人?亚洲人?谁料这一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覆盖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地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要这样写: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一位蒙恩的罪人。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从此这样存活、见证,直到安抵天家。
2008-5-19,夜宿成都文化公园。
2017-04-22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