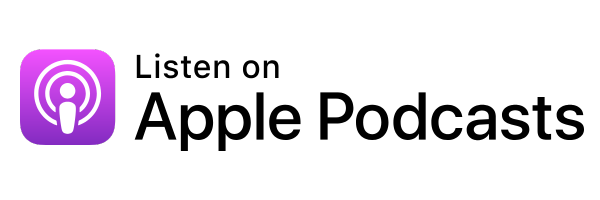我先谈谈 whisper 提到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这是我对 whisper提问的理解。我始终相信,言辞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初对文字的迷恋也是从审美的迷恋开始。除开言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意义,我对汉语写作本身,对文字本身依旧保持着这种迷恋,和对一种文字水准与品质的挑剔。
我下面再讲这种挑剔。最近余世存在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理事选举时,也提到了对汉语写作本身的关注。但是独立笔会的宗旨,是捍卫写作自由。能不能把前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审美的要求,而把后者理解为一个政治和公共维度的目标呢?在我眼里,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两者看作一回事。或者说,我更喜欢强调它们不可分别的那一面。我反对把它们割裂开来。
如果以语言为中心,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和语言之间的距离,一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前面主要是前现代的困境,后面主要是后现代的虚无。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更多关注后面的。但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和言语之间,站着什么?
在我们和言语之间,公共权力和对这种权力的畏惧,对我们的文字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个人认为这种伤害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更没有被写作者自觉和诚实的反省过。这就涉及到洛之秋提出的胡平对犬儒化的评判,以及网络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有助于抗拒还是加剧了犬儒化。
譬如很多人瞧不大起杜导斌甚至焦国标所代表的那种网络知识分子的语言。这种看不起里面有一种极其虚伪的傲慢。和自诩理性而端起来的矜持。其实回头去看民国报纸上的政论。类似焦国标的其实更多。但我们对尖锐产生了晕眩感,和策略上的排斥。晕眩感正是对审美观的自我审查。
我喜欢焦国标。尽管他的很多观点我不以为然。国内或海外,宪政或民主,妥协或偏激,公共或私下,我们都有太多所谓策略所谓定位所谓效果的考虑,其实我们惟独缺的就是本色。精神的自由不是一个遥远的前途,而是当下的状态,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才不枉此生,才可能安身立命。这就是书生意气。我最喜欢人家评论我,就是书生意气。不然要是那个遥远的前途一辈子来不了。这辈子不就活得太郁闷了。
要论文字轻薄,事实上知识分子们的写作,包括小说家和诗人,甚至包括新闻周刊的记者们,他们的语言大多都是轻薄的。作家学者们的轻薄为文,比焦国标们其实更甚。焦国标是轻薄共产党,多数的写作者是轻薄自己而不自知。我甚至读王安忆的《长恨歌》,读余华的《活着》,往往偶尔一两句话跳出来,那种在自己叙述对象面前人格的轻薄和卑微,也会一下子升到涨停,达到令人作呕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自己的叙述对象时都是轻薄的,是自我矮化、自己出卖的;只要这叙述对象触及到了现实,只要这现实足以将自己捆绑。妥协和策略固然重要,但很容易使自己陷在其中了,失去本真的判断力和同情心。这样一个卑微的人,遑论审美观呢。
我曾评论杜导斌先生,说他的文章一开始的特征就是言词锋利,像古龙笔下的人物,出手就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他的语言原则是英美诉讼中的言辞原则,是一种直接证据。我们的文字也许是更优美的,因为我们是金庸世界中老奸巨猾的写作者,我们说的话都是传来证据。因此我们擅长迂回曲折的表达。审美和学术,是知识分子沉醉于犬儒化或为这种犬儒化辩护的两个堡垒。本来是怯懦,经过这两幅盔甲,反而变成了骄傲。
施特劳斯有一个关于“隐晦表达”和“直白表达”的区分,其实隐晦是政治给予的一种限制,或者说命运。换个说法,审美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要诚实的认识到,专制主义的限制,是汉语写作实践及其审美观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学者和作家是全世界最擅长隐晦表达的一种动物。隐晦表达的传统带来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的语言成就,和审美上的一波三折。人家的文字是经历的,我们的文字都是听说的。
在今天的中国,语言的就是政治的。我也欣赏美文,但是美文里面,有一半的份额,不过是专制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当我们和言语之间,站着独裁者时。写作不可能是超政治的。超政治是可耻的,是轻薄的。
当年的朦胧诗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朦胧仅仅是审美觉醒的产品吗,朦胧也是专制的产品。朦胧诗在文学史上的推出,是以审美上不够朦胧的、在我们和言语之间用更大力气把专制者推开了的那些作品的被扼杀、被排斥相一致的。“不够朦胧”是什么意思?白痴才会认为是不够审美。政治参与了诗歌的筛选,审美也参与了政治的筛选。他们共同把黄翔这样的诗人,把我的朋友陈墨先生写于 1976 年的《天安门垮了》这样的诗,在审美史上都省略掉了。今天,他们继续省略杨争光这样的诗人。我们今天面对言语和知识分子的写作问题,不能对这种共谋没有了解,或者继续以审美的名义傲慢下去,拒不承认自己的怯懦。
关键不是你非要描写政治、描写现实,关键是站在我们和语言之间的那个阴影。有没有各人心里最清楚。贾平凹最近在小说《秦腔》的后记中谈到这个问题,谈得比较诚实。因此我有另一个评价标准,即便当汉语写作作为一个单独目标时,什么样的写作有助于缩短我们和语言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和我们笔下的文字更加亲密和自由。那种写作就是我所认同的。我们需要审美,需要优雅而有穿透力的文字。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是如此匮乏。但另一方面,你要承认,当统治者是一个魔鬼的时候,审美也是一个魔鬼。
滕彪归纳的第一点说得很对。权力是政治的,但权力对语言的伤害,其结果不一定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审美的。所以专制社会里面,纯文学是不存在的,因为权力参与了我们的审美观,造就了我们对于文字的“审美正确”(借用政治正确一语)。我们看到什么文字会摇头晃脑,一个荒诞的事实是,专制者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有股份的。所以关注政治还是关注语言,在我眼里就是一回事。不同在于关注点,是要拯救语言,就要拯救政治。或者是要拯救政治,就要拯救语言?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到此为止了。我想回答洛之秋的问题,“自我设限”还是“甘冒风险”,究竟我们如何选择?
“自我设限”还是“甘冒风险”,从策略上讲,这是个分寸问题。我这一年来的确被封得很死,也许是我的分寸没有掌握好。但分寸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讨论的,而且这就像 K 线图一样。对风险的评估和担当,就会直接影响风险本身。所以我没有兴趣分享如何拿捏分寸的问题。策略和分寸也是导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魔鬼之一。对我来说,有时候觉得,分寸就是地狱。我们需要策略,就像我们需要审美。但策略绝不能成为一个坐标。因为不管是拯救语言,还是拯救政治。对知识分子来说,或者说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拯救自己的问题。因此到底如何选择呢?
这又涉及 whisper 和洛之秋都问到的基督教的议题。刚才很多朋友问我这一年为什么沉寂了,一是打压使我发出的声音本来就少,二是发出来的部分,大多数人也看不到。三是这种打压使我重新返回了内心,返回多年来我的灵魂在渴望信仰的途中那些挣扎。因此也有意减少了外在的写作。在这一年,我认信成为基督徒。
这个话题或许现在不能细谈。先只谈一点,信仰有两个反面。一个是堕入相对主义,一个是自我神化,是智性的骄傲(也包括审美的骄傲)。用圣经的语言说,就是“自以为义”。我说策略不是坐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卖身救母”可不可以?如果这不是灵魂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包括伦理困境的问题),那就根本无所谓可不可以。
这半年,我一直在思考罪、爱、惩戒这几个观念及其关系。自由主义在中国,最近的趋势有两种。一种是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大多数人如此。以契约论为例,把宪法解释为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不过就是商业契约的延伸。这是卢梭的无神论契约论,或者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在这种理解模式中,没有罪的概念,连审美意义上的罪感都没有。爱的本源就出不来,正义的本源出不来,甚至惩戒的本源也出不来。于是宪政本质上就是策略,就是分寸。人间的审判是什么,也是策略。在相对主义中,拯救不了政治,也拯救不了语言。
李敖在北大演讲中的自由观,就是典型的世俗化的和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核心就是返求诸己。返求诸己的实质就是“自以为义”,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大的难以克服的诱惑。我是义人,我自我修行。他的说法,在制度层面上,从权利化的法治下的自由,向着黑格尔式的精神性的自由大后退(尽管他也提到宪法的权利清单,这是张佛泉 1954 年在台湾提出的观点,也是《自由中国》群体的现实诉求)。也就是从英美宪政观向着欧陆思想大踏步后退。在灵魂层面上,则舍弃求诸神的拯救,向着求诸已的逍遥和自我拯救后退。也就是从基督教背景下的残缺的自由,向中国儒道传统为支撑的圣人人格后退。李敖式的自我拯救,千百年来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自以为义的道路。端庄起来,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以求不朽。放肆起来,就是狂狷之道。看上去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叛逆。其实只是“体贴肉体”的两个方面。而圣经却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那么洛之秋说,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光想着自我拯救,否则公共二字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我要问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立言、立功、立德”传统下的公共性有什么区分呢?
这说到另一种自由主义,是超验的和有神论的自由主义。这是我一直秉承的自由主义,即英国古典的自由主义,或清教徒的自由主义。也是和保守主义非常相近的一种自由主义。这种超验的自由,不是康德的哲学式的最高精神,而是信仰和生命意义上的。因为没有最高价值则罢,如果有,对个体来说,这种最高价值与个人生命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最高价值带来对“幽黯意识”的觉察,带来人的顺服或者说认罪。否定了任何自以为义的道路。而个体的认罪有两种意义。一是在神面前,领受了恩典,领受个人的就赎。一是在众人面前,也就是在“公共”或政治的意义上,开出了一种卑谦、残缺和幽黯意识下的政治哲学。
只有这种政治哲学才有能力带来宪政的实质,也赋予我们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的正义性。一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国家主权观,二是道裂为三的国家权力,为什么要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只是一种效果,权力的分立本质上是承认国家权力的残缺。承认真道不在地上。三是法官和人间的审判权,必须从舍弃对神的全知全能的模仿和对实体正义的僭妄为出发点。这一切都为神和源自神的超验价值的临在留出了余地。所谓虚君立宪,虚人民而立宪。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虚位以待的政治神学。虚就是缺口,人不承认自己有缺口,就没有灵魂的救赎。政治共同体不承认自己的缺口,就是专制。反过来看个人,什么是无神论呢,无神论就是对自己的专制。我理解法治社会的实质是什么,是罪人对于源自神的爱与公义的秩序的效仿。只能是效仿,而不是创造。宪政的实质是什么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地上的国家就必须有缺口。天上没有神,地上的国家在本质上就不需要限制,需要的只是圣人以神道设教。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一切宪政制度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宪政和限政的区别在哪里?后者是策略,前者是本体性的。宪政其实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追求宪政,对我来说,是爱和公义的要求。也是我在大地上寻求拯救的道路,这个道路敦促我不能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一个关注公共政治的知识分子。
但一年以前,我的出发点还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我以前常说,我之所以在言行上做了一些别人认为是有风险的、在世俗眼光中看来也是有所谓担当的事。只是因为我受不了被限制,我天生是个不愿意被强权约束的人。我不说这些话,我心里不舒服。所以要说要写。但是一年以来,当我所承受的某些压力越来越大,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给予我的责任愈来愈重。譬如说很多人找你,你其实很懒,就想睡个懒觉,不想做那么多事情。前段时间我在滕彪家里,也看到他那种状态,介入一件维权案子就会跟着许多责任。累得不行。那么公共的问题首先还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的力量从哪里来?凭血气的力量,能走多远,不要说公共,就是爱你的老婆爱你的父母,你若看待自己是一个源头,你又能走多远呢?我逐步感到了自己的疲惫和无力为继。然后感觉到纯个人主义立场的虚无,它不能支撑对公共政治的担当。更不能支撑一个人在这种担当中的谦卑、诚实和公义。要知道,历史上凡是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担当中堕落的。
《诗篇》说,“那看顾以色列的耶和华是永不打盹的”,但我们要打盹,要疲软,也天生就想要放弃。
我的问题是,当我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或传统意义上的良知,都不能源源不断的给我力量,给我一种可以超越时间、超越肉身灭绝之上的正义感。如果我只是感觉不自由就不舒服,万一我以后觉得很舒服怎么办。我受过压力,也付过个人代价。但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给我自己这样一种自信心,这种生活方式是出于一种对真道的顺服,而不是出于骄傲?出于对人生的偏见和误会?虽然人也都有虚荣,但虚荣和骄傲,能支撑我走多远的能量,显然比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力量更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比我的受限制是不是导致了我对公共空间的责任更关键。责任如果是人加上去的,人就可以卸下。意义如果是人所赋予的,意义就可以修改。我对自己迄今为止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认同,需要对一个不能卸下、不能修改的源泉的认同和顺服。唯有顺服能使我跑完我当跑的路。我对这样的源泉充满饥渴的心,也对自己的放弃的可能,始终满怀了恐惧。
我不是对有神论的知识分子和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在公共效果上进行比较。就像我认为,无法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去衡量信徒和非信徒。对我来说,个人主义的力量无法避免身心的疲惫。这种肉身的疲惫,导致对个人价值世界的反复冲击。
这是我个人一年来的真切感受和认信的路径。所以有一次我对朋友说,感谢中宣部,让我有了一个机会从繁多的公共写作中脱身,重新面对我属灵的困境。
回应 whisper 的质疑,信仰本身不会自然带来宪政主义的制度成就。事实上,宪政在西方的确立过程,同时是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超验价值,受到人文主义挑战而不断世俗化、不断弱化的过程。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但幸运的是在这个围绕基督信仰的传播和挑战过程中,人类最终得到了一套制度成就。如果现在一切重新起头,那就真是地上的乌托邦了。从传统的意义上和普通法的意义上说,也的确是反文化的。但今天中国的幸运,是在主后的两千年传统之上转型,我们要的是制度的沿袭,精神的重建。罪人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西方的宪政传统给了我们可以依赖的路径,把自由问题分成了两半。而中国过去一百年的灾难就在于反过来,是精神的沿袭,制度的重建。那才是现实的、不可救药的乌托邦。
另外,宪政主义的形成,主要在英美。的确基本上是由清教徒在福音主义的旗帜下开创的。英美的特点就是超验价值传统与经验主义的法治理想的完美结合。基督教的遗产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被人文主义和自然法传统被继承,而不是像在法国那样,被观念和身体的双重暴力彻底替换。德国和法国在政治制度上都是失败的例子。假如没有英美的清教徒传统,欧陆的失败甚至将完全没有修正的机会。
回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上。刚才有人说,爱和正义的要求,听起来太稀松。的确,这两个最令人惊讶的词,因为过于完美,在我们口中却显得太平凡。那是因为这两个词本来就不是描绘人的,人没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在人那里,如果找不到这两个词的源头,那就多半是借口,或者是策略,或者凭肉体的力量,走到哪里算哪里。我们的爱,只是爱的赝品,我们的公义,只是公义的倒影。所以假如不摆脱人文主义的框架,就无法在爱和正义这两个词中欣喜若狂。我在信仰之下,对上帝属性的理解就是爱、公义和信实。并且是醍醐灌顶的经历。我对整个政治、社会和法律观念的看法,也都在重新聚合中。这个话题也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诺之秋对我作为一个信仰者的同情的理解。
问题回答不完了。因为很多问题有关联性,所以都在这里说,更清晰一些。给不能专门回答的提问的朋友道歉。
再从最初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回答洛之秋的问题。网络有没有造成知识分子进一步的犬儒化?这个诱惑是有的,也是大的。但我想,迄今为止,网络对中国知识界有几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彻底终结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我的看法,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才是虚拟的,就因为“学术化”为双方提供了表达的策略和空间,也提供了语言的障碍,在我们、我们的语言和真实世界之间,造成了断裂,也最终造成了失语。老百姓的话说,说到最后脸都憋红了,说不出来话来了。网络空间的出现,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那些实质,以“言论”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拉近了我们和问题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和危险和官方底线之间的距离。结果是什么呢,一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获得了道义辩护。二是刺激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行动热情。到今天,维权派,几乎成了自由派的同义词。甚至公共知识分子,也几乎成了自由派的同义词。
三是一个民间的意义场和评判标准的形成。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知识分子们将无法避免一一的被这一个评价系统过滤。我坚持认为言论是真实的力量,不是虚拟的。这五年来网络的发展已经表明,中国真正的政治空间的形成,将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尽管目前从网络到现实的转变还远远不够。这不是“圣人以神道设教”,拿虚拟的宪法去争取真实的权利。就像无中生有,弄假成真。这其实是信仰的结果。就像我前段时间在一份呼吁中指责地方政府时说的,“你们天真的以为这种诅咒没有力量吗”。祝福和咒诅都是真实的,审判和赦免都是真实的,这是信仰,这也是现实。
最后对朋友们表示感谢。我打字不是很快,回答很不充分。表示歉意。今晚就到这里,希望其他问题我可以下来后慢慢给予回答。我在制度的转型上是乐观的,在精神的重建上则是几乎悲观的。我说的重建,不是离开人类共同传统的重建,而是中国传统向着基督精神的顺服。这上面我的信心是小的。大概神也没有给予我那么大的职分和才能。我的道路和职分,还是在关注宪政制度的转型上。人靠着信心,做人能做的事。既然是人能做的,就没理由悲观。但人要知道什么是人不能做的。
谢谢大家。谢谢洛之秋。
[注]2006 年 11 月 5 日晚 19:30 至 22:30,王怡先生来到“如故论坛”(RGForum),和网友们就互联网、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基督教、写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本次沙龙嘉宾王怡先生在线发言的文字整理版。如故沙龙。
2006 年 11 月 5日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