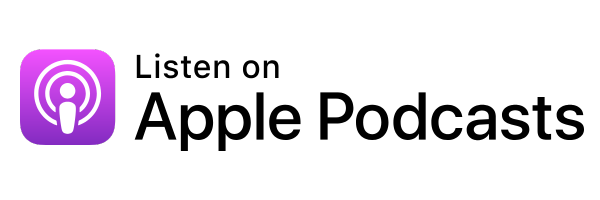在1949年前的中国,宣教士做了大量传福音及怜悯的工作。他们是主亲自差派的、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的仆人。在今天的三自系统中,仍然存在一个官方的、统一口径的说辞,称宣教士们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并不相信,但这个不是重点,就像他们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却宣称教会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有点讽刺的是,今天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里,重新研究宣教士对19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成为一个热点。甚至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的观点,都日趋积极,认为宣教士对中国有卓越而积极的贡献。反倒是那些卖主的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不好意思改口。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基督徒的知识界,通常比较在意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各方面。但他们不会关心教会本身。他们反而对教会的“非教会的功能”评价越来越高。举例来说,现在,知识分子们对司徒雷登的看法越来越正面了,而司徒雷登的神学是很糟糕的,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但知识分子们不会关心这个。而在三自系统中,其实他们的官方神学和司徒雷登是很相似的。但出于政治原因,他们还是站在党的一边,对司徒雷登持负面评价。讽刺的是,有时候主子的立场变化了,走狗们还在坚持,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十几年前,胡锦涛曾经一连几次提到了几次石门坎的伯格理。结果,整个三自系统和宗教局,上上下下都显得不自在,尴尬得很。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所以,无论教内教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用认真和合宜的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西方差会在1949年以前,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他们与中国建立起来的本土教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教会的治理结构和与西方母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教会跟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之间,这个更大范围内的政教模式和政教关系,那一代的宣教士们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第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内部的自由派神学运动,对在华宣教的负面影响。第二是20世纪初之后,整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包括西方国家的兴起和膨胀。西方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到文明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它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于是在49年前,中国教会出现了一种反抗宣教士对教会的治理和掌控的运动,叫自立运动,或者也叫三自运动。最初倡导“三自”原则的,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倪维思。他认为,差会要尽快帮助中国教会,实现经济上的自立,和堂会的自治。虽然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个金钱、文化和社会各层面的落差。但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填补这个落差。因此不应该在经济上给予本土教会过多帮助。也不用将传扬福音与改变中国社会的目标,过于捆绑起来。这也就是表明说,宣教士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地教会,使本地教会尽快独立。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保罗每到一个地区宣教,都是在该地区最大的城里建立教会,最后一个阶段性的终点就是在当地选立长老,按立长老,使他们成为教会的监督,然后“就把他们托付给神恩惠的道”。然后他就去下一个地方了。这样一个完全地方化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虽然,自养并不意味着否认彼此的经济帮助,因为保罗不断地鼓励那些稍微富有和平安的教会,甘心乐意的捐助那些贫穷或动荡的教会。自治也不意味着对大公教会的教义权威的割裂,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是要传给各地的教会去遵行的。
然而,按这个标准看,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宣教士来华一百年后,尚未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由本地牧师和长老来治理的、自养的独立教会。这时,在东北和山东,都爆发了复兴运动。尤其是山东大复兴后,出现了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虽然更多的布道家来自福建。这一批本土牧师,在十年之间,基本上取代宣教士群体,拥有了对中国教会的属灵权柄。这样,自立教会运动就开始了。这个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西方差会,和脱离主流宗派。在某个意义上,教会的这个潮流,和整个中国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是一致的。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丁立美,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会处,耶稣家庭,这些本土新宗派层出不穷,影响力日益增强。另外还有大宗派中的自立运动的联合,诚静怡是代表人物。到1930年代,“中华基督教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差会和宣教士在整体上,已不再是中国教会的主导力量。
事实上,以王明道为例。共产党进城之前,无论是从跟共产党体制的关系,还是从跟西方宣教士的关系来讲,王明道都早已成为中国本土化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基督信仰的内涵外,在教会论的层面上,王明道的确和“帝国主义”已经没有了半毛钱的关系。他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事实上,是以一间地方堂会的独立主权,去拒绝整个国家的集权主义体制的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一度认为共产党不会对他动真格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1955年6月,他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到8月份,他们夫妇二人和其他一些同工,就在一个主日的晚上被捕。公安翻墙而入,用一把手枪抵住他的腰。王明道在里面一度跌到,失去勇气,承认了政府加诸在他身上的反革命罪。随后被放出来。王明道第一次出监后,慢慢恢复了信心和勇气,重新站出来,否认自己的认罪。三年后,他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
这样,共产党以王明道为突破口,自他以后,不加入三自,就足以构成反革命罪。从这时起,“家庭教会”就意味着反革命。这就是家庭教会的诞生。因为家庭教会的别名,就叫“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随后几年中,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人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包括各地支持王明道的,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和他一样公开宣称不加入三自运动的,退回到家里聚会的。也包括虽然反对三自、但并没有退到家里,仍然在会堂聚会的。因为那时会堂还是教会自己的。各地情况复杂,但到了1957年后,你若还在三自运动以外,你就完全不可能有会堂了。
也就是说,在1955年8月王明道被捕之后,不加入三自,就是非法的。因此,我把王明道的被捕和他发表的这篇檄文,作为家庭教会运动诞生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很多人说,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零星的家庭聚会。那些不愿在三自爱国反帝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又不像王明道有独立的会堂的,就自己开始私下的聚会了。但他们在之前的家庭聚会,尚未在法律和政治上被中共正式视为“反革命行为”。直到“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及稍后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三自以外的家庭聚会,才在政治上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因此,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起源于1955年8月王明道的被捕和随后的全国性大逮捕。今年是王明道被捕60周年,也是家庭教会60周年。
杨:我觉得进行一下梳理非常好。确实在1949年以前,就像你刚才说,已经有了基督教的自立运动。最早可能在20年代,就已经出现个别的自立教会,后来出现了一些像王明道这样的福音堂,比较独立的教会。也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教会系统。比如倪柝声的小群聚会所。还有山东的耶稣家庭,还有中国特有的极端派别,像真耶稣教会。他们实际上真正实行了一种自立、自传、自养,跟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有一些交往但不受其指派。而在1950年开始推展、到1954年正式成立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那些参加“三自”运动的,恰恰是有西方宗派背景的教会。这些宗派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紧张的。在三自运动中被迫害的,恰恰是真正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其实也受自己对政教关系理解的影响,他们和他们本国政府是什么关系?如何看西方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再一个就是他们与中国基督徒的关系,我想有多重因素。西方宣教士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不是很一个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