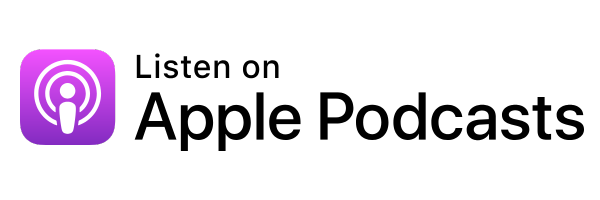主所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下麵是我 3 月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由崇基學院和“中國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講座。4 月,也是北京守望教會戶外聚會三周年紀念,謝謝他們的編輯整理了這場講座的錄音,登在三周年戶外特刊上。最近,江浙的許多三自教堂,也面臨政府拆十字架和拆教堂的行動。我將這篇長文作為牧函給你們,請你們常紀念那些捆鎖中的教會和肢體,也深知道你們各人各家所蒙的恩召,無不與教會在整個時代的使命與處境緊密相連。
一
請允許我先分享一段經文。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講了施洗約翰臨死前的一個故事。他身陷囹圄的時候,派人去問耶穌,我們等待的彌賽亞到底是不是你啊?“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施洗約翰是為耶穌開路的先鋒,是宣告耶穌是彌賽亞的人,他曾給耶穌施洗。但是現在,這樣一個人卻來確認耶穌的身份。也許因為他處在個人的困境中。他也許在想:如果你真是彌賽亞,快點讓我出去啊。我怎麼能因為相信你,做你的使者,卻淪落到被殺頭的地步呢?但更重要的是,他陷入了信仰危機。其實約翰很願意自己衰微,耶穌興盛。他並不在乎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就要結束了。只是他聽過耶穌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而這些都超越了他對彌賽亞的理解方式。因為耶穌說他與父原為一,說他有赦罪的權柄,
說他是亞伯拉罕的祖先。這與約翰宣告說亞伯拉罕的後代中有一位要來,看起來是矛盾的。到底祂是不是彌賽亞呢,或者說,他到底是一位怎樣的彌賽亞呢?約翰不是派人來向耶穌求救,而是在死之前必須確認耶穌是誰。換句話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然就死不瞑目。並且這也意味著,在任何政治處境下,一個人要問的首要問題,都是耶穌到底是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看起來並不能救命,但卻能決定生或死的意義。
換言之,教會在世上的一切政治挑戰,都必須根據福音本身來回答。而耶穌的回答有兩個重點。
第一,耶穌指出約翰在掙扎。約翰因為耶穌的自我宣告而被冒犯,他對彌賽亞的認識被顛覆了。耶穌說:第一,如果你因為我而掙扎、而困惑、被冒犯,但你卻不因此而跌倒,你就有福了。第二,耶穌暗示說,如果我不是你們等的那一位的話,你們就將永遠等待下去。要麼你已等到了彌賽亞,要麼你就要永遠等待戈多。
1978 年後,右派被平反,幹部恢復工作,補發工資。那時的中國歡呼一片。人們不禁對鄧小平問道:“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轉眼到了 1989 年,趙紫陽身邊聚集了一大批渴望改革的人,在那個春夏之季,他們也在急切地詢問:“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待別人呢?”
之後二十年來,不管是胡溫上臺,還是習李上臺,這個問題一直重複、縈繞在神州的上空。整個知識份子群體,甚至包括基督徒知識份子,都保持著兩個根深蒂固的心態。一個是期待“明君”跟“賢 王”的心態,背後代表著他們對地上的國度的期待。在這個期待中,我們可以來探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的國跟地上的國的關係。因為這顯然跟非基督徒去理解地上的國,或理解個人自由與群體自由的關係有所不同。因此,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基督徒如何面對這個時代的政治挑戰,這和整個社會當如何面對時代的政治挑戰,應該是不同的。但是,當許多教會和基督徒也在追問和反思這個議題的時候,卻反映出幾乎同樣的對“明君”跟“賢王”的期待,及背後對一個地上的國度的期待。這一點很可悲,顯
示出我們對地上的國度與那個看不見的或靈魂的國度的關係,仍然需要反思或調整。
第二個心態,中國的基督徒,甚至是其中的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是個很曖昧的概念,到底哪些人可以稱為公共知識份子,很值得探討——無論如何,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間,仍有著強烈的“帝師”心態。我想,在香港即使知識份子們希望某個意見被議會採納,但因為政府中已沒有一個可以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被稱為帝王的角色,所以也不能簡單稱為帝師心態。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處境下,90%的知識份子們都程度不一地抱有這樣的心態。他們不是站在跟政治國家相對應的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的立場和角度去評說和建設,而是極其強烈地站在政治國家跟帝王的角度,去為他們著想,或由此決定民間的回應模式。甚至要求他人也站在這個位置上為帝王著想。“你想想,他
有多難呀!”“你想想,習近平能怎麼做呢”?等等。他當然有他的難處,他們也有他們要考慮的問題。不過知識份子們,仍然普遍缺乏一種在基督教神學的歷史上稱為的“兩個國度”的視野,或者在政治學上稱為“政治國家”跟“市民社會”的二元視野。中國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包括基督徒在內,都仍然沒有把自己放在這個二元模式之下去看待社會的變化。更缺乏從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關係出發的歷史觀和自我認知。當然,的確有人處在離決策層更近的位置上,有機會出席一些所謂的高級會議,聽到領導放出來的一些氣球。就如最近,教會從趙曉弟兄、梁燕城博士那裡,不斷傳出一些好消息(福音?),一些宗教政策要變化的資訊。我無意於評價哪個預測對,哪個預測不對。但我看到的是,我們的心很容易被權勢系統所主宰,所驅使。以至於“帝師”的心態與“明君”的期待不斷復活,失去了我們要提的真正的問題。
劉軍甯先生,曾對比這種中國人的“帝師”心態,與舊約中的“先知”角色的差別。他很正確地指出一件事,帝師都是在宮裡,或期望進入宮裡(在某種意義上,社科院也是“宮中”的一部分)。但先知都在曠野和民間。或者說,“宮廷先知”(或者也叫政協委員)都是假先知,“曠野先知”才是真先知。
約翰是一位曠野先知。他與君王的關係,是一個國度與另一個國度之間的二元關係。並且,他與君王的關係,將取決於他與耶穌的關係。這就是當他身處政治迫害的時候,不是向君王、而是向耶穌發出“那將要來的是你嗎”的詢問的原因。
從家庭教會來講,她在中國過去這半個世紀,已經提出了那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並且已經確認了答案,這個答案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因此,教會已經而且必須站在一個非常確定的國度的視野,來看待她所面對的一切政治挑戰。但我們有時候會受試探,離開所站立的國度,以致於在對政治的回應中忘了教會是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我認為,家庭教會在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並不是肉體的逼迫,也不是任何外在權利的喪失。教會面對的最大的政治挑戰,始終是不知道自己是誰,失去了教會對自己的屬靈身份的認知。從而在一個政治與教會的關係模型中,也失去了看待政治挑戰的福音化的視野。
換言之,教會對她所面臨的一切政治挑戰的回應方式,如果促進了教會在中國獨立於政治國家之外的自我身份認知,這樣的回應就是好的,是上帝所喜悅的,是福音所定規的。為這個緣故,教會不惜失去一切,包括身家性命。就像約翰身陷獄中卻不求搭救一樣。反之,如果教會的回應方式,加劇或維持了教會與政治國家的混同(或和諧),或將教會的身份和信仰置於政治國家的範疇之下或之內,這樣的回應就是糟糕的,是反福音和反教會的。
二
美國二十世紀的神學家尼布林,曾給政治下了一個定義。他說,“一個社會的形成就是政治”。有一個一百人或五百人的聚集,並不代表就有一個社會。好比我昨天到香港,我的航班出了故障,後來他們派了一個很大的波音 757,把延遲的三個航班的人一起塞了進去,差不多坐了四五百人。但這四五百人並沒有形成一個社會,雖然他們中間碰巧有一些社會關係。這兩天大家都在關切馬航的失聯飛機。假設一架飛機遇到空難,墜落到一個孤島上,像美國的電視劇《迷失》。當飛機掉在島上的時候,若掉下去有二百人,他們就會經歷一個形成社會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做政治。他們當中,碰巧也有幾個人是互相認識的,碰巧有幾個人是老鄉,碰巧大家還能說同一種語言。這會讓他們互相之間連接互助,可這些都不足以形成一個社會。
只有兩種方式可以形成一個社會。第一,假如有人從駕駛艙裡找到一把手槍,他就可以建立一個社會。當年的羅馬,或者 1949 年後的中國,就是這樣形成的。第二種方式呢,在《迷失》中,很有意思的情節,就是有一個叫洛克的人,他是個癱子,上飛機時坐著輪椅。結果墜機後,他就站起來奔跑了。他跑去砍樹。別人問他,你在幹什麼,他說他要去修一個教堂。這是很有意思的象徵,因為它反映了整個西方社會——就是在過去這兩千年,從五旬節開始,從福音傳到羅馬之後的整個西方社會——的形成過程。五旬節,或者說基督的教會,就是形成一個社會的方式。
五旬節聖靈降臨,代表著一個新的社會、甚至是一個新的城邦的形成。耶穌升天之前選定了十二個使徒,其實當時只剩十一個,所以他們一定要做一個預備工作,就是把第十二個人揀選出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教會裡有五個長老,如果有個長老生重病,或者在信仰上跌倒了。我們不會說,一定要選一個人來補他的位置。至於將來我們看到一個弟兄很合適,決定再增選一個長老,但這並不是為要補上一個長老的位置。意思是說,即使剩下兩個長老,加上牧師,所組成的長老會仍然是合法的。但是十一個使徒,卻一定要再選一個人來替代猶大的位份。為什麼呢?從神學上講,因為十二個使徒代表著整個以色列,代表著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代表著那個要擴散到地上萬族、分散到各國裡
去的基督教會的合法代表。在憲政的意義上,或者說在盟約的意義上,你可以說,十二使徒就代表著全體教會,所以一定是十二,十一就沒有任何意義。十一就等於零,十一就是非法的。所以這十二個使徒就代表著那個新形成的社會,新形成的那座上帝之城,一個在地上的、眼睛看得見的社會。到了五旬節,因為一個超自然的上帝之靈的工作,這個新社會形成了。那一天約增加了三千人。這三千人就聚集在一起,他們天天在殿裡、在家中禱告、互相擘餅、用飯,甚至賣了田產房屋,等於建立了一個“公社”。在廣泛的意義上,教會成為了政治國家之外的、第一個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
當然,她首先是一個屬靈的信仰共同體。聖經以奧秘的方式稱之為“基督的身體”。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他們也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共同體。如果你來對照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歷史背景,你會發現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為在當時的羅馬,在西元前 27 年,屋大維開始稱為元首或叫第一公民,我們通常管他叫第一個羅馬皇帝,這意味著古典的羅馬共和國消亡了。在西元前後,羅馬的共和制度消亡,轉為了帝國體制。這是主耶穌的時代背景。但在五旬節建立教會的時候,卻發生另一件相反的事,就是這十二使徒代表了一個新的、政治國家之外的“共和體”。你會發現,在教會外,舊共和消失了;在教會內,新共和誕生了。這就是尼布林所說的“一個社會的形成”。教會,在本質上是一個共和的社會。
她的根基是信徒與基督的屬靈的聯合。這是共和的第一重意義,即她建立在一個神聖的盟約之下。其次,信徒通過眾長老的議會制,形成了這一神聖盟約之下的看得見的共和體。這個信仰中的共和,跟那個正在消失的政治上的共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背景呢,因為它對我們從基督教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在一個無神論政權下所面對的政治挑戰,提供了思考的模型。在當年的羅馬,是從共和到帝國;在今天的中國,是從帝國到共和。而我們還沒有完成這個過程。今天的中國其實是一盤散沙。社會不是在形成中,而是在潰散中。像梁漱溟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特徵只有個人,而沒有社會。換言之,除了槍桿子出政權外,我們缺乏“形成一個社會”的能力。尤其是形成一個神聖的和宗教的社會的能力。我們也都知道,當代中國的總體問題,仍然是政治國家過於強大,而市民社會過於弱小。現代化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國家的轉型。但是,政治國家的轉型並不是取決於“明君”和“帝師”。而是取決於在政治
國家之外,有沒有新的社會的誕生?在中國的“第三共和”來到之前,是否有一個“屬靈的共和”的擴展?
這種擴展在本質上聖靈和福音的工作,而在政治學上考察,則是一個哈耶克所說的“自發演進秩序”的擴展。從人類的有限經驗來看,在政治國家之外的那一個屬靈的新社會的形成,才可能真正帶來政治國家的良性轉型。
這是西方基督教歷史的總結。第一,沒有教會,其實就沒有社會。在羅馬帝國整個衰敗跟結束的過程,甚至到了歐洲的所謂黑暗時代之後,你非常清楚地看到,有教會才有社會。當羅馬失去皇帝的時候,如果沒有羅馬主教,文化和道德意義上的羅馬就徹底消失了。第二、教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第三、教會在這個末後的時代,也一直身在社會當中。所以我們始終必須面對的,用基督教的神學術語來講,就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的二元關係,它們既對立,又重疊,代表著今生和永世,肉身和靈魂的爭戰。用一種世俗的政治學理論來說,就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關係。我們需要在這個架構中,去理解教會在中國所面對的政治挑戰。
其實當邢福增教授為我定這個題目的時候,似乎已經把教會放在一個有點委屈的地位了。我們很可憐,因為我們似乎必須面臨這樣的挑戰。我們總是落後挨打的一群,我們總是被逼得到處跑的一群。但是在上述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一直以來,家庭教會、尤其是城市家庭教會都是對政治國家的祝福。政治國家需要教會所帶給它的祝福,遠勝於教會需要政治國家的保護或確權。好像我跟宗教局幹部在一次談話的時候(我在溫州被他們騷擾),說到登記問題。我就跟他講,第一,家庭教會絕不會在宗教局登記;第二,我們也期望有一天可以在民政部門登記,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區分了宗教類或非宗教類的 NGO 組織之後來登記。我又說:第三,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們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之前,教會還是教會;但是在教會沒有到民政部門登記之前,民政部根本就不是民政部。因為民政部還沒有完成它的現代化轉型,民政部只是掛了一個牌子,它實際上還是清朝的戶部。它若想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政部,就必須等到我們在那裡登記後才能幫助它成為民政部。意思是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教會對合法性的需求,遠遠不如政府對合法性的需求大。我就跟他們講,不是你們幫助教會走向合法化,是教會要幫助這個國家走向合法化,是教會需要和願意以她的受苦去幫助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所以,教會雖然面對政治的挑戰,但政治其實也一直面對教會的挑戰。這也是為什麼我提出一個理論叫“三次文革”。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第一場文革是打擊基督教跟其它所有宗教。所以第一場文革是“對宗教的文革”,從 1951 年開始,在基督教內的三自反帝愛國運動,其它的封建迷信、反動會道門派,也都一起端掉了。第二場文革是針對資本家的,到 1956 年完成的經濟上的公有制和集體制轉型,消滅了資產階級,我稱為“對經濟的文革”。第三場文革是從 1957 年開始針對知識份子的運動,這是“對知識的文革”。最後,1966 年的文革,主要指向黨內,是一場“對黨內的文革”,當然那也是一場波及面最大、最全面的文革。因此,你會非常發現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後,所面對的第一個合法
性挑戰,就來自教會;對一個無神論政權而言,沒有比教會更大的政治挑戰了。中共首先把宗教當成第一號敵人,它先搞定有信仰的人,然後搞定有錢的人。至於那些沒有錢、又沒有信仰的知識份子,擊潰他們是輕而易舉的,因為他們是無根的階層。
今天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知識份子和一般民眾,仍然不會把宗教(信仰)排到比較靠前的領域中,一定是政治最重要,或者是經濟掛帥,或者是知識萬能,而不可能是宗教最重要。但我們看共產黨在1949 年執政之後,按尼布林所講的定義,它是如何完成一個新社會的形成的“政治”過程的呢。並不是打完天下就自然有一個新社會,一定要透過一個廣義上的政治過程去形成這個社會。而形成新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壓迫宗教,第二步是剝奪有錢人,第三步是羞辱知識份子,最後才進入狹義上的政治範疇(黨內奪權)。有一次我和一些知識份子朋友這樣講,我說這會不會讓你有一點失落,就是原來你並沒有自己想的那麼重要。對共產黨來講,又沒錢、又沒有信仰的人其實不那麼重要,是排在第三位的。在人家眼裡,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才是第一位的。
因為這就是現代國家的特徵。現代國家產生於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而不是產生于文化與政治或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從建政開始,就一直面對教會帶給它的政治挑戰。因為它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新的統治模式,是古代社會沒有的”。有些學者也講過類似的話,就是自由是古代的,專制是現代的。阿倫特說,這種極權主義跟我們古代看到的那些暴君、那些奴隸制社會都不一樣。為什麼?因為現代的極權主義是把自己的整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它的意識形態的“偽神學”的根基之上,這種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使國家本身成為一種宗教。這就是極權主義不同於歷史上的一切專制或暴君統治的原因。這是阿倫特說,
為什麼極權主義是一種直到 20 世紀才出現的最邪惡的人類統治模式,就因為它使國家本身成為一種宗教,成為“活著的上帝”(黑格爾語)。它也使這個國家的治理者成為一種“祭司”階層,它所建立起來的是一種現代的政教合一國家。
因此,對這種極權主義來講,它面對的最大的政治挑戰,就是基督的教會在人類歷史上不間斷的存在。就是從五旬節之後的那個新的共和,在希臘、羅馬的世界一直到現代社會中的擴展。所以,請讓我這樣講,共產黨體制對今天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來講,的的確確構成一種政治挑戰。但我們必須反過來講,家庭教會,尤其是正在興起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是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最大的政治挑戰。一直以來,政府都可以很快地鎮壓和瓦解其他一些社會力量。直到今天它都自認是成功的。然而,1949年以後,它唯一的敗績就是面對教會。在這六十年中,它從來沒有打贏這一場仗,它從來沒有贏過耶穌基督。甚至當它可以用最厲害的肉體消滅的方式時,政府都沒有打敗過教會。更何況今天它只能夠使用一些間接的方式,甚至在身體的逼迫上它的手段也要受制於更複雜的社會經濟情形。因此,表面上看,家庭教會一直都在被打壓,一直都在受虧損,一直都是失敗的,直到今天仍沒有一個合法地位。但另一方面,像北京的守望教會,幾位牧師、長老被關在家裡,耗上三年,也沒有把一個群體瓦解掉。我所接觸到的所有員警或宗教局幹部,我都發現他們已經失去了雄心壯志,沒有一個人會覺得執行這個任務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們消滅,或者讓你們解散,關門,坐牢。他們心裡根本已失去這樣的勇氣和信心。因為在與教會超過半個世紀的交手中,失敗的其實一直都是政府。
在某個角度上講,守望教會的事件,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就是政府決定要滅一夥手無寸鐵的人,搞了幾年,卻沒有把他滅下去。連逮捕的行動都沒有。這不可能發生在今天的政治犯、上訪者或其他任何異見人群中。事實上,在這六十年來,你找不出第二個例子。為什麼,因為教會在本質上是一個已經形成的新社會,是一個基於信仰而聯合的屬靈的共和體。而知識份子的背後呢,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尚未成年的市民社會。如果金天明牧師不是牧師,而是一位異議分子,早就抓起來判刑了。你是劉曉波也可以抓,你是高智晟也可以抓,你是許志永也可以抓,事實上你是誰政府都可以抓,不但抓了,判了,而且的確可以殺雞儆猴,保上十年太平。但是抓金牧師卻沒有用。這不是因為他了不起。是因為你無法把他的主人抓起來。在四川有一個朋友跟我說:“我覺得你是最危險的,最應該抓起來的,怎麼每次都不抓你呢?”在過去幾年,這也讓我很傷心,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朋友都坐過牢。但為什麼沒有抓我呢(也許就快輪到了),也不是因為我了不起,是因為我的主人是耶穌基督,我的背後是主的教會。抓我是很簡單的,但抓我沒有用。抓英雄有用,樹倒猢猻散。但抓僕人有什麼用呢,主人派來的第二批人更厲害。抓了我,教會就升級換代了。政治國家付出的代價更大。所以 1949 年之後,逼迫的結果帶來教會的不斷增長。正像馬禮遜離世之前,面對寥寥幾個信徒,他說:“百年之後,必結實百倍”。這是一個鐵的定律,二千年來,顛撲不破。政府是看在眼裡的,逼迫三十年,教會差不多增長十倍,又逼迫了三十年,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增長了多少倍。
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中國的城市家庭教會,在今天面對政治挑戰時,我們需要首先看到自己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的聖潔身份,看到我們作為一個不同於政治國家的一個屬靈的新城邦,一座眼睛看不見的城邦的意義。同時,教會作為一個信仰共同體,事實上扮演了未來的市民社會的一個雛形和樣板的角色。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持守和捍衛這個獨立的屬靈身份和獨立的社會地位,用表面上的失敗和虧損,去面對政治挑戰,並且帶著祝福未來的中國社會的心。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已經構成了對我們所在的國家的政治挑戰。這正是彰顯福音的機會。失去了這個獨立的屬靈身份和獨立的社群地位,就失去了復興的機會。這是我想分享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三
中國社會過去的這十年,我們對它的評價,始終要從兩個很基本的東西來看。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共產黨體制是政教合一的體制,是一個不放棄對人的靈魂、信仰、精神的控制與教化的一個政權。
所以我們觀察它的變化,首先要看宗教自由的變化,看政教合一的程度上的變遷,看它有沒有削弱它在社會中的“祭司”身份,它有沒有削弱對社會成員的信仰跟思想、精神的控制?那麼,我的結論是,過去這十年,中國沒有任何變化。
我既不認為,它有相當明顯的倒退,也不認為有任何明顯的改善。實際上,十年來,中國仍處在一個威權體制與寡頭體制的平衡點上。因為這涉及到中共統治的關鍵性領域,什麼是關鍵性領域呢?
宗教就是關鍵性領域,因為它觸及中國政府的全部合法性基礎,和整個政權的基本性質。所以它跟教會的關係,是決定它生死存亡的關係。它可以反貪,也可以一下子對農民很好,可以在體制的某方面做一個很大的改動,給老百姓一些實惠。這些古代的君王統統都有做過,但這些改革或不改革,都不會涉及這個政權的本質,不會涉及到它的本質,就不會帶來它真正的變化。
從這樣一個角度講,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裡面,你看到,“宗教自由”被界定為所有的人權和自由中的“第一自由”。中國很少有知識份子能夠認識和承認這一點。甚至在教會中,很多教牧人員跟基督徒知識份子,也不一定深入認識到這一點,並且基於這一點去看到教會與整個國家的關係。在 2009年,守望教會,和我們秋雨之福教會,都有被政府取締後上街的戶外崇拜。那段時間,我看到一系列的國內非基督徒學者的評論文章。其中我要再提到劉軍寧的一篇文章,他這篇文章就叫《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寫得非常好,雖然他還不是基督徒,但他是一個對基督教的價值有很高認同的保守主義的政治學家,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看見教會戶外崇拜事件的意義。非常肯定地指出,宗教自由在中國的社會轉型跟人權運動中,是處於一個核心的基石的地位。所以,無論是過去十年,還是習李上臺這一兩年,我們都沒有在這方面看到任何鬆動,在這方面沒有鬆動,其它鬆動都等於零;在這方面沒有鬆動的話,其它方面的鬆動都是暫時性的。總之,對一個現代國家的政體來說,最重要的議題就是政教關係。政教關係不變,極權主義永遠是極權主義。
第二點就是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在這個方面,中共體制的本質是中央集權制。但這不是共產黨的特點,這是秦始皇以來的特點。所謂“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從這個方面來講,政治上的變化,取決於中央集權的性質有沒有鬆動。事實上,經過經濟市場的開放,地方在不斷得到它實際上的主控權的增大,那是因為它有錢,這是市場帶來的。但是十年來的每一輪改革,每一屆新政府上臺,都有一個相同的政策走向,就是收拾地方大員,重新在政治上“削藩”,然後進一步將中央集權體制再一次穩定下來。無論是江上臺,胡上臺,還是習上臺,你都會發現這個特徵。每一輪中共換屆,一定要幹掉一個地方大員。不幹掉一個地方大員,就沒有辦法重新穩定中央集權體制。第一次“削藩”是北京的陳希同,第二次是上海的陳良宇,第三次是重慶的薄熙來。但同時,你會看到地方大員對中央的逼宮與威脅,在每一次換屆中也越來越厲害。中央收拾他們、重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的穩定性,花的代價也越來越大,後續的政策也會越來越強。這是習近平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全稱)的原因。不是求改革,而是求穩定。
當然,總會有很多人繼續著對“明君”的期待,就是等他坐穩了之後,會放手一搏鬥。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我是一個牧師,不是一個政治學家。我只知道無論他會幹什麼,我們從這個政權最基本的兩個特徵,一個是政教之間的模式,一個是中央跟地方的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點沒有任何變化,第二點只有加強、沒有削弱。因此這個極權體制仍然是鋼性的,它不會呈現出任何出人意外的、人們所期待的民主和開明的變化。當然在廣泛的經濟和文化領域也許會有改革,但那些變化是不需要政治改革的,那些變化主要是政治力量之間角逐的結果,那些變化是歷代的皇帝——當他覺得時機到了——他都可以去做的。所以這是我作為一個牧師,對中國社會的基本評價。
四
在過去十年,在知識份子或公共媒體中,我們已經很難再提“憲政”的轉折,也很難再提“民主”的轉型,甚至很難再用“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字眼來描繪未來的方向。但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治理轉型”這個概念。你會發現,整個中國社會,從國家到公司,從教會到其它民間組織,大家都在面對一個治理轉型。這也是我想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政治挑戰,或反過來看教會對政治的祝福的議題。
剛才和幾位牧師在一起,也分享到這個題目。我以前有一句很不好聽的話——我屬於家庭教會,也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所以我也批評家庭教會,是因為我愛她。就是在中國的家庭教會中,弟兄多的教會的治理,就像《水滸傳》;姐妹多的教會的治理,就像《紅樓夢》;老弟兄比較多的教會的治理,就像《三國演義》;靈恩派的教會治理,就像《封神榜》。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這些人被神得著了,被聖靈聚集在一起。可是福音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上帝的子民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使我們形成一個屬靈的城邦。雖然在末世,這不是一個眼睛看得見的、有刀劍權柄的城邦,但它的的確確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真實的新城邦,這個城邦在政治國家之外存在著,又存在於一切政治國家之中,並且反過來對政治國家產生挑戰和影響。
這個基本模式,是福音的,也是末世論的。她影響了後來的整個西方社會的治理文化。但是中國教會的治理,顯然更多是受中國文化跟中國傳統的影響,而不是受聖經的影響,也不是受兩千年教會歷史、及改教運動以來的新教傳統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講,你基本上會看到,美國的教會是怎麼治理的,美國的政府就是怎麼治理的。因為這就是是美國建國的過程。美國還沒有立國之前,已經有長老會和浸信會,浸信會(或早期的公理會)向美國提供了民主的原則,長老會則向美國提供了代議(或共和)的原則。所以在北美大陸上,尚未形成聯邦政府之前,那一個已經形成的新社會就是教會。那一個已經形成的新社會裡面的治理文化就是浸信會跟長老會(我在這裡只是拿浸信會和長老會作代
表),它們在民主的原則跟共和的原則上,塑造了整個美國的制度和治理文化。反過來看今天的中國呢,那就要反過來說,中國的共產黨是怎麼治理中國的,中國的教會就是怎麼治理教會的,中國的企業就是怎麼治理企業的,中國的 NGO 就是怎麼治理 NGO 的。甚至,中國小學裡的班長和學習委員就是怎麼當班長和學習委員的。實際上,外資公司和基督教會,是當代中國社會僅有的兩個攜帶了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治理文化的載體。少數的外資公司裡面,帶有一種新的商業機構的治理模式跟文化,但它的數量較少,影響較窄,仍不能構成對整個中國社會治理文化的改變。而教會幾乎就是唯一的,有可能改變中國治理文化的社會共同體。
當整個社會的治理都面臨轉型時,今天的城市新興家庭教會就面對著一個相當重要的、福音化的使命,這是以前的鄉村教會沒有面對的,就是他們開始注重教會的治理,他們開始向著建立一個有美善的次序的堂會轉型。這意味著宗教改革的教會觀,將影響和塑造家庭教會對宗教改革的福音的理解和認識。原來的鄉村教會也在做這個工作,但是城市教會在這個工作上是起頭。這對教會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同時對政治社會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
於是我們看到,城市家庭教會,需要一種以福音為中心的植堂運動,不單單是從個人的意義上去傳福音給 A、A 給 B、B 給 C,而且需要形成一個植堂運動,以“教會”本身來傳福音,以聖約群體的擴展秩序,來回應當代中國的政治轉型與挑戰。當一個基督徒向人傳福音時,不單是告訴他人,自己信主的奇妙的內心經歷和個人深刻的悔改經驗。並且告訴他人,自己現在活在一個共同體中,那是中國人從未經歷過的,一個真正的自由個體之間的聯邦。一個“屬教會”的基督徒會告訴他人,自己的自由、情感、生命,都已融入在這個群體中,這個群體才是真正的、大隱隱於市的桃花源,這個群體不完美,但唯有這個群體,指向一個將來的、完美的社會。一個新社會已經形成了,或者更準確地說,
是一個新社會已經降臨了。這正是信徒可以繼續活在一個糟糕的舊社會中、可以承受苦難和虧損而不再憤憤不平的原因。
我是期望,看起來也會如此,城市家庭教會正在發生的治理轉型,必須先於中國政治國家的治理轉型。上帝給了我們機會,應該走在政治國家的前面,應該成為一個屬靈的“新共和”,反過來挑戰這個國家的“假共和”,也反過來祝福和塑造未來的中國社會形成一個新的共和體。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國社會,教會並不具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因為大家都已在一個成熟的社會背景下。如今的教會也不見得比其他機構更成熟,在所有構成市民社會的機構裡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在今天的中國不同。除了教會,你基本上就看不到其它成熟的市民社會裡面的組織跟結構,這就是為什麼異議分子都可以抓,但是抓牧師還是會謹慎得多。真正的原因就是除了教會之外,你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就找不到這樣一個有組織的公民共和體(感謝主,相比之下黑社會的規模和組織程度都太低了)。換言之,在一個虛假的中國社會中,只存在一個真實的公民社會,那就是主耶穌的教會。作為數千萬之眾的、真實的公民自由結盟的共和體,教會是中國社會裡唯一存在的真實的共和體。因此,反過來說,什麼時候家庭教會有一批牧師被逮捕,什麼時候真正的變化就可能來到。所以我們不要去問政治家,那將要來的是你嗎。如果在十字架上被殺的耶穌就是那要來的。祂已經來了,帶著肋旁的傷口。那麼城市家庭教會就要準備好,不是去迎接高層人士傳出來的利好消息,而是去迎接下一波的、黎明之前的逼迫。
五
今天的城市家庭教會,可以懷著祝福整個政治進程的心。這種祝福不是指我們要跑到街上示威遊行,更不是要進入一個狹隘的政治空間,而是我們要以國度的眼光來看政治,政治就是一個公共社會空間,政治就是一個新社會的形成。一旦地上有了基督的教會之後,政治就一定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的一種二元對立、重疊和互相爭戰的複雜關係。
換言之,這種意義上的政治,其實是福音的禾場。這種意義上的政治,就是國度與國度的關係。
而教會必須在這種關係中才能清楚和守住自己是誰。我們不可能屬於宗教局,不可能屬於統戰部,不可能被政治國家置於它的內部。我們命可以不要,錢可以沒收,但必須與政治化的教會(所謂政治化的教會,就是放棄長子的名分、而屈服在政治國家和無神論宗教體制之內的教會)一刀兩斷。
從這一角度來說,教會面對的政治挑戰還有一點,就是靠著信心除去心中對政治的一切懼怕。因為整個中國公共生活裡面,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怕”。事實上,中國社會最主要的一種公共政治情感就 是‘怕’。懼怕構成了全體中國人——無論官員還是商人,無論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個對政治的態度。很多人不敢來教會,是因為政治上的怕;很多人離開教會,是因為政治上的怕;很多人不敢參與服侍,是因為政治上的怕。事實上,這是城市家庭教會面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挑戰。
我歸納一下,第一個政治挑戰是失去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認知和社會上的屬靈地位;第二個挑戰就是面對我們內心的真實的懼怕。我曾在北京認識一個 1989 年坐牢的民運人士,他後來信了主。他說曾經很長一段時間,他去過不同的家庭教會,但教會都不接待他,因為他去了之後,牧師就告訴他,下次不要再來了,因為你一來,就把員警引來了。
我必須說,就基督教傳統而言,這是很荒謬的事。因為在教會歷史上,你會發現,把員警引來,基本上就是教會的目的之一,也是教會復興的方式之一。中國的家庭教會一直就是一個“不從國教者”的運動,它裡面有一種屬靈的勇氣;但是我對此仍然會有批評(再次強調,因為我屬於家庭教會,對她的批評絲毫不意味著對她的否定)。我必須說,在整個中國家庭教會中,屬靈的勇氣很多時候是被誇大了的。其實所謂家庭教會的傳統,裡面除了有真實的屬靈的勇氣(這是被上帝的恩典所保守的),但還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底色,就是“怕”。其實,“怕”一直就是我們作為罪人最基本的底色,這個底色一直蘊含在家庭教會和廣大信徒、包括傳道人的心中。讓我們承認吧,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擺脫恐懼。我們從來就沒有單單因著福音,而在一個無神論的極權主義體制下得著真正的自由。然而我也必須讚美主,因為家庭教會的歷史表明,我們在那裡軟弱,我們就在那裡剛強。懼怕並沒有讓家庭教會在整體上走向失敗,這是主的恩典,並且僅僅是主的恩典。
最近這十年,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幫助我們開始逐步地、除掉對政治的懼怕。好像《加拉太書》5 章 1 節中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如果基督徒和教會因著信仰而有一種自由,相信這種自由甚至是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的一切自由的前提,相信即使法律上的全部自由都被剝奪了,而這種自由卻是剝奪不了的。因為這是中國歷史跟中國文化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一種自由,那麼我們就需要不斷地活在福音當中,不斷地認識福音,不斷地向施洗約翰那樣,在困境中再次發出那個問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如果是你,我就一無懼怕;如果不是你,我就還要繼續懼怕,我就必須從牢裡逃出來,不然我就白死了。
反過來說,如果耶穌是基督。我就不能繼續懼怕,也不需要繼續等待明君和賢王。不然我就白活了。
以前,作為一個自由知識份子,很多人也誇過我挺勇敢的,好像不怕事,所以我比較瞭解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坐牢,甚至妻離子散。事實上,政治犯是中國社會中離婚率最高的群體。我曾經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理解、甚至敬佩他們當中的勇氣,這種勇氣使得他們在很多時候比中國的絕大部分基督徒更加有一種道德感染力。我遇到過這樣的朋友,包括劉曉波先生。我也給他傳過福音,但他跟我講過一句話,說:“在你們教會裡我沒有看見一個值得我尊敬的人。”他這樣說,我就不好說了,因為這表明我本身就不是他尊敬的人。當然,歸根到底我認為他還是太驕傲了,連他的謙卑和寬容都太驕傲。但這是他個人需要面對上帝去解決的問題。而在另一個角度,我們的確發現,教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裡,並沒有呈現出一種不懼怕的見證,在中國精英的知識份子(我說的精英不是指他有職稱或在社會上有地位)、在那些道德和文化上對這個社會有擔當並因此受虧損的那一批人面前,我們的確沒有贏得他們的尊重。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在學問上、功德上去贏得尊重。我的意思是,他們沒有在你身上看到你所宣稱的,有一種自由你們已經得到了,你們是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而我們是一群不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教會沒有讓那些還在追求或者無望的人看到這個差別。因此教會所面對的政治挑戰,就是要不斷去挑戰我們心中和整個社會上對政治的懼怕和敏感,以及我們內心的怯弱,和對這個社會在公義、憐憫上的極其巨大的虧欠。因此我所服侍的教會,在這些年間,我們希望不斷去突破一些界限,通過這些界限,也不斷地幫助弟兄姊妹去突破他們內心對社會和政治勢力的懼怕。
過去的五六年中,我們發生過六起弟兄姊妹退黨的事件,每次這樣的事件對教會都是一個震動,對他們所在的單位更是巨大的震動。這些會友都經歷過許多壓力,然而我沒有看見過比他們更被聖靈充滿的信徒。他們的收入、職位,受到極大的影響,但沒有一個真正是被開除的。
在這些年,我們也公開地從事良心犯家屬的援助事工,在過去幾年已幫助了十幾個良心犯的家庭。
雖然在這個義工小組的弟兄姊妹只有六七位,大部分教會成員都不會和這個事工有關。但所有人都知道,因為有了這個事工,我們所有人都有某種危險,他們都知道要共擔風險,要在禱告和奉獻中共同承擔。這個良心犯家屬援助小組裡,大概有四五位曾坐過牢的基督徒,我們教會中有過監獄經歷的信徒,幾乎都在這個小組裡服侍。
我們的上訪者團契也是一樣,義工大概有十來位,但是整個教會在這裡面,都會經歷到一個除掉懼怕的過程。
最近兩年,我們也開始一個反墮胎的事工。其實在此之前,有好幾個家庭因為生養多胎而受到過逼迫,承受了許多壓力。去年,我們在兒童節發放反墮胎的單張,有七位弟兄姊妹被帶到警察局。
所以有一些臨時來我們教會參加敬拜的弟兄姊妹,在彙報時偶然聽到這些事工,有些人感到很害怕,不適應。因為大部分中國人都不適應。事實上,也的確有一些會友因此而離開,選擇去“安全一點”的教會。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相信教會的講臺,是當代中國社會中言論自由度最高的講臺。在中國,沒有哪個大學教授,沒有哪個新聞記者,也沒有任何一個公民結盟的講臺,能夠單單基於他的信仰和良心,而在除去任何外在恐懼的情勢下講話,或不因政治勢力的無形威脅而影響和調整他所要講的話。城市家庭教會的講臺,必須成為中國社會言論自由度最高的講臺,必須成為中國社會的良心自由的所在,必須除掉一切的政治懼怕,單單以信仰和良心來生活、服侍、宣講,並祝福自己所在的城
市。當你向你的被共產黨和 CEO(有時他們是重疊的)所統治的鄰舍,傳講他們是一個罪人的時候,當你向他們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時候,你必然在這個社會真實的文化、政治處境當中去傳講。若你懷著對政治的懼怕,或對世界的諂媚,你就不能去面對這個世界在政治意義上對你的信仰發出的挑戰,你就沒有辦法來塑造新一代的基督徒,你無法使他們形成一個新的社會,攜帶著新的社群的基因,去拓展福音的國度,並且去祝福這個淫亂和慌亂的社會。
(本文是王怡牧師今年 3 月 8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座,限於篇幅有部分刪節)
2014 年 3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