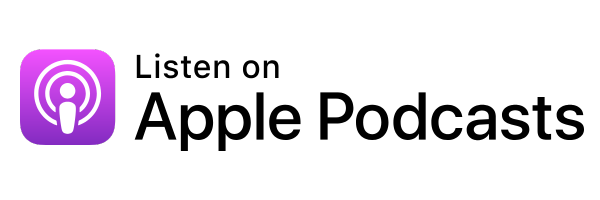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 24:1)
一、改革宗的世界观场景
从我们的本分、或人蒙福的回应的角度讲,改革宗神学最强调的是圣徒的敬虔。从三一上帝的角度讲,改革宗神学最强调的乃是上帝的主权并对万物的恩典性的护理;其中最重要的护理,则是上帝拣选祂的子民,为他们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
《诗篇》24 篇描绘出神,就是那一位宇宙的王和全地的神,并祂的全能与荣美。《箴言书》8 章 22 节,说到创立世界以先,“就有了我”。直到 30 节,说“我在祂那里为工师,日日在祂面前踊跃”。则谈到创造时那一位宇宙性的基督。那永恒的智慧,即神的道。也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在人类历史中成就救恩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新约的《以弗所书》1 章 4-10 节,同样讲到那位宇宙性的基督。在未有世界以前,并万世以先,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再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成为一。这是从一位宇宙性的基督,论到救赎的宇宙性的果效。换言之,固然只有神所拣选的子民蒙恩得救,但救赎的果效与目的,却及于整个宇宙。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得救,就指向整个人类的得救;而人类的被救赎,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被救赎。这并非普救论或死后二次得救的可能,因为在上帝的主权而非人的视野里,世界一部分的被遗弃与整个世界的被救赎并不冲突。但改革宗的世界观,的确与普救论共享着一个基本的宇宙性框架,即我们只是“万物中初熟的果子”。个人得救,和狭义上的广传福音(即狭义上以十字架为内涵的福音,而非以整本圣经的整全真理为福音),在欠缺宇宙性框架的神学中,被视为圣徒事奉的终点。这是一切圣俗两分的起源,却并非圣徒所领受的全备使命。
在路德高举以十架为中心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时,他其实与大公教会(天特会议之前的罗马教会),依然共享着一个稳定的基督教的宇宙性场景。他是在一个未曾被撼动的世界观场景中凸显救恩论。而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则面对基督教世界观即将迎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主义、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的兴起),重新描述了整个宇宙性场景。
神在万事万物上的掌管,眷顾,显出祂永恒的旨意。这预旨和预定,不仅指着我们的得救而言,其实圣经经文所指向的那幅图画,超过圣约群体本身的得救。
圣经不仅是论到谁得救、谁没有得救,都在永恒中有一个美善的预旨。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最在乎的问题。但对神而言,对整个宇宙而言,谁得救、谁不得救,并非最关键的议题,显然也不是神在圣经中要我们以全部思虑都去挂念的那个核心。从这个角度说,预定论并非改革宗神学的中心。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是针对阿民念主义的错误教导针锋相对归纳出来的。单从五要点出发,其实尚不足以在整体上描述一个基本的宇宙场景。改革宗神学的根本之处,是以一种彻底的有神论,即 100%的有神论,来理解这个世界。如司布真所说,“在加尔文主义与无神论之间,没有安全的立足之地”。
我以三点,来描述这一圣经世界观的基本宇宙场景:
第一,这世界是神的,不是我们的。神要在被造的世界中建立他的国度,彰显祂的圣洁荣耀。这才是整个宇宙的主题和历史的主题。宇宙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一辈子的主题就是什么。不然我就成了这宇宙的造反者。
第二,这世界也是我们的。因为神主动施恩与我们立约,并透过所立的圣约,使我们被造、堕落和救赎中进入神的国度。因此这个世界也在一种被托付和被肯定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的。即我们要去治理的,要去爱惜的,要去宣教的,要去更新的,也要在肉身中去存在和经历的。一个方面,这肉身中的世界并不等于神的国度;另一方面,这肉身中的世界与神的国度也并非完全断裂。因此,也可以说神的国度透过成就在地上的救恩(主耶稣的十字架)和活在地上的圣约群体(新约教会),也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第三,神透过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这全然败坏的人洗净、挽回,带入恩约之中,并赐下在这个国度中敬虔生活的法则。这些法则出于神自己一切美善属性的要求。而这一切皆出自神恩独作的主权性的恩典。
这一幅基本的图画,是我们一切神学与实践、敬拜与事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基本框架。
二、历史和肉身中的平衡
我们因神的话语而信,因信而理解,知道这个宇宙从永恒到永恒,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非常确定、非常肯定的目标与走向。我们的任何选择,这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叫神惊奇,都不可能落在祂预旨以外。这是一个在我眼里变幻无穷、但在宇宙论上确凿无比的天父世界。能将这变幻偶然与确定稳妥之间连接起来的、神赐给我们的唯一纽带,就是对基督的信靠。如果这纽带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我们就是禅宗或诺斯替主义者。如果这纽带不存在,我们就是怀疑论者。
我们因祂的话语,靠着圣灵光照而知道这是真理,并确信和投奔这样一位神。
改革宗的神学传统,带出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当比其他神学与属灵传统中的信徒,更有蒙福的确信和直面的勇气。在罪人的本位上,我们理当更加恐惧战兢;从永蒙保守的地位上讲,我们的生命光景,当在基督里有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但人的事奉若不够,人被神恩激动的程度若不够,这种预定论下的安全感就可能转化为属灵的骄傲。平衡就在处境的艰难与内在的确信之间。换言之,预定论是上帝说给那些事奉得很艰苦、在处境里挣扎得很艰难的的圣徒说的。对那些不事奉的信徒,或事奉得很舒服、很得意的圣徒,上帝则宣讲祂的浩大与难测的主权和恩典。神的恩典与主权,是比预定论更基要的真理,神对子民的预定与拣选,不过是这一宇宙性场景的理所当然的结论之一。
改革宗教会应该有一个对普世教会更加包容的牧者之心。不是牺牲立场,恰恰是因着立场的确定。唯有改革宗神学能为基督徒提供一个完整的知识论。就是在“我相信”和“我知道”之间,因信而有一个确信,我不但相信,而且“我知道我相信”;我不但知道,而且“我相信我知道”。而唯有这一完整的知识论,才能为教会提供一个全面理解和进入当代中国社会,更新文化土壤的信仰根基。
当然基督徒父亲知道要有恩慈进来,基督徒母亲知道要有真理进来。但教养的路,就是我们自己成圣的路。我想这也是神要我们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的原因之一。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若非神特别的恩典,是不能单独生养教导敬虔后代的。
我学习教养孩子和学习牧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生命里难有平衡。一个改革宗的父亲跟一个改革宗的父亲,还是真理大过恩典;一个改革宗的母亲,还是恩典大过真理。惟独在基督那里,真理跟恩典完全合一。在他身上,既有为父的心,又有为母的心。纯正教义与敬虔生命完全合一。我初学习改革宗神学、初在讲台服侍时,更多把自己当作教导者。后来慢慢心里生出牧养的负担,神的呼召叫我进入全职的牧养,我才看到自己生命和服侍中的五个失衡:
1、真理与恩典之间的失衡;
2、公义与怜悯之间的失衡;
3、教导与牧养之间的失衡;
4、劝勉与等待之间的失衡;
5、悔改与安慰之间的失衡。
改革宗传统对敬虔的认识,对敬虔主义最大的差别,在于圣洁与公义的关联。
敬虔主义的圣洁观,可能跟个人有太直接、太内在、甚至太神秘和难以捉摸的关联。但改革宗所持守的圣洁,一定和公义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没有公义就谈不上圣洁,而公义则与社群有关。在我的领受中,改革宗神学最宝贵的有四点,这四点本身是平衡的,但在我个人的生命与事奉中却不总是平衡的:
1、上帝的至高主权,透过永恒中的预定和历史中的护理,成就祂自己的荣耀国度;
2、全然败坏的个人透过悔改与信心的回应,白白领受恩典的救恩论;
3、蒙恩之人传扬全备福音的使徒性事奉;
4、蒙恩之人持守圣洁公义的先知性事奉;
三、对当代中国社会与家庭教会之场景的认识
讨论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即教会之于社会的公共意义的彰显。基于改革宗的世界观,首先需要认识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C.S.路易斯曾说,“我们要有两重的倾听,一重的倾听是永远倾听神的声音,即圣经的真理;另一重的倾听就是倾听这个世界。要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知道这个世界今天的潮流在哪里。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的偶像在哪里”。如果不认识世界,基督徒就很难让那个在肉身中显现的道,去挑战、回应和施恩于具体的处境,文化和人心里的偶像。
简单的说,中国处在李鸿章所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今天,这一两千年未有之转型,150 年来的民族道路,乃至 1949 年之后 60 来的转型,及 1978 年后 30 年的转型。都将在最后的几十年中完成,包括制度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道德的转型,以及最核心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观的转型。
改革宗神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是为这个时代所用的。
最近 500 年的世界历史也很清楚,奠定了今日全球之信仰、文化、社会与政治面貌的那个一千年未有之转型,发生在十五、十六世纪,与改教运动同时。在那个时代,罗马教会已无法面对这个世界核心价值观的巨大转型。教会悖逆了福音真理,已无法继续为未来的世界场景,提供从圣经真理而来的支持与祝福。恰恰在那时候,神兴起了改教运动和归正神学。直到加尔文主义这一重新被描述的圣经世界观的成形,祝福和影响了近 500 年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框架。上帝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兴起改革宗神学,人只能在他的位置上倒因为果地看,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两千年未有之转型,即将在这一代及下一代人当中,完成核心价值观及文明范式的定型。如果我们相信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真理、一个对圣经整全真理的历史性的表述。我们在中国教会中,就当以最大的信心带出牧养的心,即对中国教会的牧养性的使命。今天的改革宗教会跟改革宗同工应有一个更大的眼光,即我们对中国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有一个牧养性的使命。
要以整全的真理和圣经世界观的看见,去牧养神在中国的教会,服侍这个核心价值观转型的时代。
第一、面向中国教会,承担牧养性的使命;
第二、面对中国社会,承担先知性的使命。
当许多教会缺乏整全的信仰,将福音狭窄化或廉价化的时候,改革宗的传道人,应像施洗约翰一样在旷野中发出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呼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谁是站出来指责罪恶的人,如果不是改革宗传道人,还会是谁呢?向君王发出悔改呼召的人,如果不是改革宗传道人,还会是谁呢。以圣经真理向着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发出悔改呼召的人,如果不是改革宗传道人,还会是谁呢。
2008 年在加州,华人教会联合起来反对八号提案,基督徒们上街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但是整个海外华人教会,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公开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中国今天最大的群体性、制度性罪恶之一,是流人血的罪,最严重的有三个方面,就是泛滥的死刑,非法的劳教和强制的计划生育与堕胎。中国社会今天最大的群体性的、制度性谎言之一,就是被禁止了20 年不准说的六四屠杀。如果改革宗的传道人不站出来指责罪恶,宣讲那公义的、讨神喜欢的准则,还会是谁呢。
就像当年诺克斯在苏格兰所扮演的先知性角色,不是因着自己受逼迫而自义,而是跟整个民族一起担当苦难,发出城中的角声。今天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和传道人若不为着主的缘故如此去行,我们的一切神学领受与装备,都难免讨人厌,也讨其他宗派中的弟兄姊妹厌。
中国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的的过程,同时也有极大危险成为一个世俗化过程。这一公开化的速度和世俗化的速度,也都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快。如果说,只有改革宗神学能为中国教会即将来临的这一公开化时代,提供一幅整全信仰下的图画与时代性的看见。那么改革宗教会和传道人,就有责任背起十字架,去担负一个以整全真理牧养众教会的祭司性使命,和在中国社会行公义、好怜悯的先知性使命。
唐崇荣牧师对文化有一个定义,即“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换言之,整个群体的价值观、世界观,他们看待人生的所有观念的总和,及这些观念所影响下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换言之,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中的群体位格内涵的相交。正是在位格内涵相交这一意义上,文化即一个社会看得见的灵魂。先知性的使命,就是上帝需要我们去看顾、提醒和呼召中国这颗转型中的灵魂。
四、改革宗信仰对当代中国五个层面的影响
第一,是在道的层面,即改革宗神学或归正神学运动。今天很明显地看到在中国,尤其在城市教会中,现在也慢慢影响到乡村教会,出现一个跨宗派的归正神学运动。程度不一受归正信仰影响的教会在中国今天的城市新兴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甚至可能成为主流之一。这是一批海外改革宗华人牧师几十年的传讲、祷告和等待,希望看到的一幕。这一幕在中国已开始和扩大。因为改革宗神学并不是一种宗派神学,改革宗神学就是新教神学。它本身是跨宗派的,在清教徒时代已经跨宗派了。它不只影响长老会,它在各宗派里面都有影响,包括圣公会和从英国分出来的各种宗派。实际上,在新教各主流宗派中,唯有改革宗神学构成了一种普世性的神学,并对整个世界的文明格局造成了数百年不止息的影响。今天在中国,也正在出现一个主要受海外归正神学运动影响的跨宗派的改革宗神学。
第二,是在宗派层面,即改革宗教会的建立。国内公开接受威斯敏斯特信条、采用长老制(或会众制的改革宗浸信会,目前仅昆明一间)的改革宗教会,据我所知已有数十间之多。更多的可能数百间的教会正在公开认信与教会建造的历程中。未来 5 年中,可能出现区会(长老会)甚至中会的连接。即出现改革宗宗派的形成。
第三,是在教会层面,即众多接受改革宗影响、但并不公开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或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加尔文主义教会。如北京守望教会,自称为“改革宗的福音派教会”。这一“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概念,是借用改革宗浸信会的表达。公开接受改革宗信条(对改革宗浸信会来说就是伦敦第一信条)的教会,被称为“改革宗浸信会”;接受改革宗神学,但并不以改革宗信条为认信信条的教会,称为“加尔文主义浸信会”。这些教会在中国城市教会中有更大、更公开的影响,成为福音派教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是在治理的层面,即长老制对中国家庭教会转型的巨大影响。在西方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的宗派格局中,长老制不会、也没有单独成为一种跨宗派的、带有普世性的教会治理模式。但整个家庭教会面临教会治理的根本性转型,并长期在带领人(一种不成熟和不确定的主教制)模式下,经历了专制主义传统对教会治理的伤害。因为名义上的会众制和形式上的主教式的某种结合,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治理的主流。但数量更多的非改革宗的家庭教会,在教会治理与建造的转型中,开始对长老制有浓厚兴趣。改革宗教会的众长老治理模式,应当也能够在当前中国教会的治理转型中发挥积极的典范作用,使长老制成为未来中国教会一种跨宗派的治理模式。
第五,是在文化的层面。即改革宗神学对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的阐释。一种完整的看待宇宙人生的态度,以及藉着文化使命的担当,对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之重大转型所发生的文化影响。以上 5 个层面,构成改革宗在中国之公共意义的一个同心圆。改革宗神学在中国今天,可能有一个在以往华人世界中前所未有之前景。即成为影响未来中国教会的正统信仰之主流。但这个主流不是从人数或规模来说的,就像新教改革晚期,加尔文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新教世界之主流,是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宗派,包括世俗世界之文明,都程度不一地受其影响。并且没有另一种神学能具有类似的影响。改革宗神学之于未来中国教会,也可能如此。
未来的中国教会,必然重新形成正统信仰中的几大宗派。但若只是简单地接回来原来的宗派,则几十年的隔绝和拆毁没有呈现上帝特别的旨意。今天,改革宗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一个很大因素是海外社会没有经历宗派被打碎的过程。而在中国今天,改革宗能够成为一个跨宗派的神学运动。而长老制也可能成为一个跨宗派的教会治理运动。因此,中国的改革宗神学与改革宗教会的发展,怎样往前走?是我不能够回答的。但我的领受和思考认定我们应当拓展视野,以这五个层面,来看待和回应改革宗在当代中国之公共意义,不要将改革宗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之巨大影响的前景,狭窄为一个简单的神学运动和宗派主义运动。但作为主流宗派的改革宗教会的建造,仍是关键性的层面,因为跨宗派的意思是要跨,而跨的前提是先要有。
根据王怡在 2009 年 5 月在福州“改革宗教牧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2009-12-14 修订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