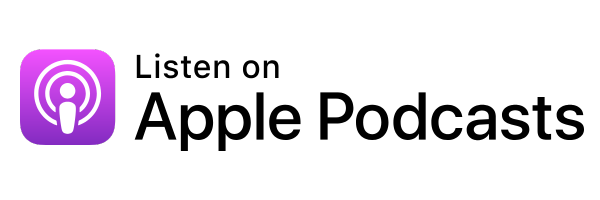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开放》编者按:2006 年 3 月,四川青年学者、著名作家王怡路经香港,对本刊介绍他皈依上帝的信仰历程,也谈到中国大陆基督教信仰的趋势,认为基督信仰是中国社会未来实现和平转型的真正盼望。
知识分子觉醒的三种情况
问:听说你是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现在一大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维权律师也加入教会,为甚么会有这个现象?
王怡:中国四九年后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知识分子们的觉醒有几种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一开始是从审美的角度觉醒,发觉共产党统治下的语言及其形式,都丑陋到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就是从审美的觉醒开始转向对自由和尊严的恢复的,这个趋势的一个顶点就是高尔泰提出那个著名的命题,“美是自由的象征”。或者像作家廖亦武说的,我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和他们的审美观不同。另一种是价值上的觉醒,即追求自由民主的世俗价值,回到五四以后一直比较弱势的那个传统,从政治上去反思、反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以及中国人在这种统治下的、失去生命尊严的群体命运。在整个八十年代所谓的新启蒙时代,就是价值的启蒙,当然也包括不断的审美的启蒙在内。
问:还有呢?
王怡:还有第三种,就是信仰的觉醒和对人文主义本身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八九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识分子们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这种追求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儒家式的、自觉担当社会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仍是一脉相承的。但把民主梦当作生命的价值本身,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一,很容易破灭,一旦发现这个梦无法实现,如八九年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精神幻灭后,就向着共产党和社会现实妥协,在荒宴醉酒的个人生命中无力自拔,躲避崇高,走向虚无,大多走向某种相对主义,没有精神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理想。这是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犬儒、向着一切罪恶投降的原因。第二,就算少数坚持一生都将民主自由奉为公共信念的人,也许不管怎样艰难,他也坚持下来了,但对苦难的崇拜,和对政治罪恶的仇恨,却把他捆绑了。在这种艰难中,越来越难以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有限性,反而可能在道义上把作为弱者的我们自己崇高化、偶像化。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理想,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证民主之后他就不会腐败变质。
问:听说焦国标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这几年大陆的知识分子,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确出现了一个走向基督信仰的趋势。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如小说家北村、余杰,维权律师群体里面的李柏光、张星水等人,更多的人也接近或开始了解基督教,包括高智晟、焦国标最近都决志信主。“决志”是说我心里确定了这样一个信靠,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无力从罪中自救出来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决志是一个开口的祷告,即《圣经》说的嘴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将来会有一个洗礼的公开见证。
从个人主义走向更高的源泉
问:你是怎样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读大学接触过《圣经》,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倒是很早对无神论有过反思,所以一直不是无神论者,但也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羡慕,也很尊敬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进到那种“境界”去。很多人误以为信仰是一种“境界”,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这几年,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作过一些个人的努力,也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赞扬,但我自己开始警惕那种士大夫的、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所以我一直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反复的说,我不是有勇气,我只是有脾气。因为脾气没有道德含义。当我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学校停我的课,秘密警察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禁止媒体发表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也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等等。我虽然没有对政治的恐惧,但却出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以前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其实是一道在信仰面前的防线。就是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呢,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我的言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担当,只是我的个人主义选择。网上曾有人评价我,说我和另一位朋友是那种“闻见不自由的味道就会扑上去的人”。但其实这句话让我很害怕,当我疲惫和无力时,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仅仅因为我的选择是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这就是信仰的开始,即对自我的怀疑,也看到了世俗的价值理想的有限性。读《圣经》,使我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罪人,是不义的人。虽然有人认为我作了一些“义”的事,连我有时也这样看自己。但我开始领受到我内心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的和公义的。但这个公义和善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独裁者面前就并没有自信心,说我相信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你们坚持的东西一定是错的。哪怕是对亲人的爱,其实也不是从我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不可能是那个源头,我只能去迎接那个源头,把我的心腾空了,去领受上帝的爱。这样我就慢慢接受基督的信仰,接受在十字架上的爱和公义。然后发现我的生活有了以前做梦也没有的改变。
两个迫害教会案产生心灵震撼
问:在你走进基督信仰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人给你传教,给你的启示?
王怡:之前我开始读《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有一些朋友像余杰等,向我传福音,我也开始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若我到北京,就会参加余杰所在的方舟教会的聚会。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也与两个教会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关系。一个是华南教会案,这是近几年中共打压基督家庭教会最严重的一个案子,二零零一年,这个教会的龚圣亮牧师和其它两人一审被中共以邪教罪、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判死刑,整个华南教会有六十余人被判刑或劳改。去年四月华南教会两位姊妹到成都来,其中一个是龚圣亮牧师的妹妹,我请她们和成都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到我家来聚会,请她们向我们讲这个教案和她们的信仰。她们讲了如何被严刑逼供的情形。一位姊妹如何在看守所被打死。那次聚会给我很大冲击,我在她们脸上看到一种圣洁的光,她们是只读过小学的普通农村妇女,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一种从未接触到的亮光,使我不相信她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像我不相信使徒彼得这样的人物,只是一个打渔的。在此之前,我也看过「十字架在中国」这套纪录片,这个片子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很大冲击,这两个华南教会的姊妹走后,就在我家里开始了查经的聚会。去年十月份,我和几个维权律师一齐前往华南教会调查他们的案子,我们与很多指控被龚圣亮牧师强奸的姊妹,以及教会的同工、信众作了完整的笔录和录像,我们看到龚圣亮和他的教会,的确存在严重的错误,看到家庭教会在地下状态下出现的偏差和败坏,但也看到了大多数信徒的虔诚和纯正。同时也看到华南教会被政府以一种非法的和粗暴的方式进行政治压迫的惨烈。介入这个极其复杂的教案的法律调查,不断地震惊和挑战了我之前的全部知识和信念。这是我逐步走向基督信仰、领受上帝给我的呼召的重要历程。
问:第二个案子呢?
王怡:第二个是去年在北京的蔡卓华牧师印刷圣经,被判 4 年有期徒刑的案子,我是辩护团的成员之一。和滕彪一起为其中一名被告作无罪辩护。我在去年参与了这两个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调查或辩护,也参加了一年的聚会和读经,最后因着神的恩典,能叫我来到他的面前,确信了对上帝的信仰。
信主之后的自由言论更坚定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无很戏剧性的细节?
王怡:的确有一个让我领受信仰的、很重要很戏剧性的事。去年六月的一天,我在家里爬梯子,到屋顶的书架最高一层翻书,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那次我缝了九针,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当摔下来躺在地上不能动那刻,我开始唱赞美诗,并开始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开口祷告。这是一个对我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经历。我那个庞大的书架,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对这种理性的自负,我半辈子就是靠着知识和理性去寻求真理,你感到自己几乎已经掌握了真理。在与一个专制政权作斗争时,你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站在道义的高峰。结果呢,我从最高处一下子就跌下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走到了理性的尽头,感到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真理的。我爬上去之前满腹经纶,摔下来之后两手空空,开始接受在我之上的《圣经》启示。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反而离上帝最近。怀着平安和喜乐的心情,这次摔跤对我的信仰有很美好的意义。
问:有了信仰后,追求自由民主事业是否会更加坚定?
王怡:接受基督信仰后,我对自由民主的思考比以前更深入了一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民主的和自由的,因为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有他的位格、尊严和自由。如果这一点不成立,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其它人待我们如同兄弟,也没有理由反对强者可以凌驾在弱者之上。我们常说共产党的统治没有合法性,你没有人民的同意凭甚么统治我?但强权者也可以说,凭甚么要你同意呢,我有枪有炮为甚么还要你同意?人与人之间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应该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上是民主的、自由的和平等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起点。但是,终点是什么呢?对我来说,终点不再是政治了。对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他不同意共产党的专制,但他对生命本身的盼望,不再和共产党有关系了。哪怕是自由和民主,也不能给一个人幸福感,不能把你从你的罪中拯救出来,甚至不能让你更有耐心的去爱你的妻子。在我看来,中国人应当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中国人在政治的罪恶中挣扎了一百年,挣扎了五千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容忍一个不公义的、不自由的社会在我眼前,而我却袖手旁观。不能容忍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在这个世代被人类公开的羞辱。信主后,我对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比以前更加清楚和坚定。我也观察到当代一些知识分子接纳基督教后,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使命感,他们大多数人并未成为牧师,但都在自己所领受的呼召中,决定把一生的事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献给自己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且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勇气,我们不能再因为这种勇气而骄傲,而是应该因此而卑谦,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的。
教友礼拜聚会通常五六小时
问: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强势,是这样的吗?
王怡:不错,趋势很明显。在八九年之前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在乡村教会,城市和知识分子中的教会很少。城市中有两类,一是海外教会差派的,集中在城市比较多,韩国和海外华人的传道人很多,台湾教会也在做大陆福音传道工作。第二类是中国乡村教会中比较成熟的,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向城市传福音增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温州教会,也有河南教会。最近几年城市知识分子团契,包括学生团契也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去年我到成都另一个学生团契中去,意外发现我有三个学生在那个团契中,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传播在城市和大学生中面还是很广泛的。现在大学生中,共产党的党员越来越多。但是感谢上帝,学生中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即使是学生党员,也有成为基督徒后悄悄退党的。这些重新找到了信仰而退党的年轻人,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问:基督教的复兴是否与中国当前价值虚空有关?
王怡:那当然了。八九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价值的虚无,信仰的真空问题,其实几千年来,我们的内心不是一直都处于饥渴状态吗。上帝在我们心里最深处留了一个空位,这个位置除了上帝自己,你拿任何其他东西去填,一辈子都填不满。一辈子都是空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的确空得可怕,共产党把中国人内心一切的美好价值几乎都拆毁了,我常常相信,上帝要让中国人得到的恩惠越多,共产党就拆毁得越多。哪个地方拆得最干净,那个地方福音就最兴旺。共产党是几千年来撒旦最卖力的仆人。这个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里把世俗的价值、普遍的启示拆得更干净呢?所以海外很多人回来到大陆乡村教会都非常惊讶,发现大陆信徒的饥渴慕义的状态,与海外教会真是不一样。我在海外也常参加礼拜天的聚会,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但在大陆,包括以前在我家的聚会,经常能到五六个小时。我在华南教会,看到弟兄姊妹们五点钟起床,读经、祷告直到八点钟,天天如此。如四川遂宁的天主教传统很深,我到遂宁步云乡调查中国第一个乡长直选,意外发现十个村就有十三个寺庙和一座教堂。佛教近年来在城市乡村的发展,包括在共产党干部中都很鼎盛。很多人讨论法轮功时也提到中国大陆的信仰真空问题。宗教的复兴在中国的确非常强势。但是价值虚无带来的,一面是信仰的复兴,一面也是偶像崇拜的温床。即使是在基督教家庭教会中,也存在各种异端和极端的信仰派别。在缺乏宗教自由的非法状态下,教会很难有健康的发展。
(采访记录经访谈人修订)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