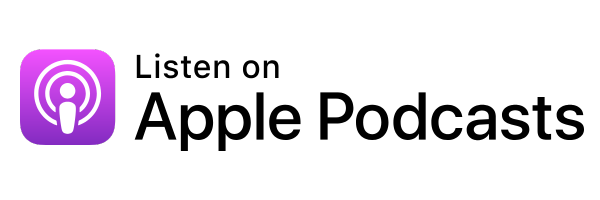在华盛顿分手,几个律师去了德州,我同另几个回国。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看了这部锋利的电影。新闻片和法庭片,是我收藏的两个拳头产品。当导演把法庭径直搬到直播厅,你想我会多么爱不释手。尽管演导编都缺少大牌,但有时只是一个构思,就激动了你的情怀。
故事也放在德州,因德州仍有死刑,小布什当年也因拒绝特赦一个死囚,而享有“德州屠户”的恶名。州长和电视台老板,策划了一出“全民判决”的实境电视节目。三个小时,在演播厅内施行审判。九百万观众,成为人群中最浩大的陪审团。芸芸众生,可以在一小时内拨打电话,点击网站,以最直观、最感性的方式,论断被告是否有罪。法官宣布死刑判决,一周后,高达一千一百万人,在网上付费观看了死刑直播。
倘若这一切是真的,大概会是继苏格拉底被 501 人的雅典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和拿撒勒人耶稣被犹太群众和罗马总督判钉十字架之后,人类史上第三起标志性的、当众羞辱司法正义的群众谋杀案。尽管被告可能真的、残忍地杀死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剧中的辩护律师叫山姆。1991 年,另一个叫山姆的美国律师,和他两个朋友回应苏东的溃败,追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异象,成立了著名的基督徒律师组织,“辩护国际”(Advocate International)。他也参与另一个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督徒法律团契”(Christian Legal Society,简称 CLS)。我去参加的,就是这两个 NGO 四年一度的“全球基督徒律师大会”。150 个国家,近千名律师、学者与会。借用 CLS 的宗旨来描述这群法律人的理想,是最恰当不过的:Seeking justice in love of God(在上帝的爱中寻求公义)。
好撒玛利亚人,是福音书中耶稣的一个寓言。旧约说,一切律法的精髓,是爱神和爱你的邻人。有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人呢。耶稣便以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设譬。说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剥光衣服,打得半死。一个祭司过去了,没有伸手;一个利未人过去了,还是袖手。一个撒玛利亚人却停下脚步,为他包扎,送到客店,将随身银两托付给店主。好比是说,一个垂死的中国人,领导先走了,书记过去了,爱国主义者游行去了,一个日本人却蹲下来救了他。耶稣咄咄逼人地问,你说谁是那需要帮助者的邻人呢。
直到如今,我们的法治观,还是立不起两样根基。一是正义,一是爱。关于前者,人们会问,正义真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吗。等于是问,世间真有正义吗。其实邻人正是一个普世性的譬喻。老祖宗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在我们中间,“人”却日益下降为低于民族政体的一个概念。法律界最可悲的格局,就是 90%的言说,都出自没有价值立场的衡量。如果非要修改一篇论文,首先被抛弃的,就是作者的价值观。就像一个大学生,如果非要考公务员,要撒的第一个谎,就关乎他的信仰。
关于后者,人们问得更直接,法律与爱有什么关系呢。在当代中国,justice inlove,是陌生到一个地步,甚至显出几分诡异的说法。赦免,也就成了一个久违的、似乎只与君王特权相关的古代概念。我们学了一个法治的形式,然后手足无措地,不知道把“赦免”摆在什么位置。
这次全球基督徒法律人的汇聚,见到三个心仪已久的人物。一是弹劾克林顿的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他演讲的风范令人着迷。一是国际监狱事工的创办人寇尔森。尼克松“水门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幕僚。在狱中,他读到路易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幡然悔改,受洗信主,成为水门事件后唯一公开忏悔的当事人。
寇尔森不但成为著名的福音派作家,也从此致力于在狱中传福音,办查经班,让服刑犯学习自我管理。今天,国际监狱事工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上千座监狱中,每年带领数千人成为基督徒。
他的故事也到过德州。小布什在德州监狱内划出一个区域,允许寇尔森的监狱团契独立管理。当年,布什州长手牵一位杀妻犯,在狱中齐唱《奇异恩典》的照片,曾广为流传。十年后,寇尔森带着这位修完圣经课程的杀人犯,进入白宫,再次与布什见面。他在书中这样写道,30 年前,我是一个背弃了国家和正义的罪人,走出了熟稔的罗斯福厅。今天,我却带着一个重刑犯回到这里。寇尔森说,多么不可思议的改变,二百年来,这是第一位服刑中的重刑犯,被允许进入白宫。
在电影中,电视台老板为操控舆论,故意设计伪证,误导山姆相信被告可能是无辜的。但在直播的最后关口,却忽然拿出谎称遗失的现场录像带,在电视上播放。山姆在最后陈词中,悲愤地对着上千万观众说,不要杀死我们的司法制度,不要判他有罪,因为正当的程序被违反了,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审判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如山姆说,请记得,你们不是决定让他去一个海岛,是要决定让他从地球上消失。所以在旧约中,摩西说,“审判是属乎神的”,《诗篇》中甚至把世上的审判官称为“诸神”。这就和英文中直接把法官称为“Justice”一样。
不确信公义的普遍性,就不理解“Justice”这一对法官的、实体正义意义上的称谓。我想,一个不信仰法律之正义的人,怎么敢一秒钟背负这个头衔呢。但一个不相信爱的永恒价值的人,也无法理解程序正义的真实涵义。爱与仁慈,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是法律的统领。justice in love,就是 justice in procedure(程序中的正义)。
我见到的第三个人物,是约翰·罗伯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二百年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这位强硬的保守派,几十年前做过前任奎伦斯特的助理。说到底,一位敬畏上帝的首席大法官,对司法体系而言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代又意味着什么。当我蹉跎几万里,落地后,听见杨佳的案子二审开庭的消息,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仍活在这两种风险之间,舆论中的“全民判决”,或现实中的“司法暗杀”。当一个仇恨社会的公民,诉诸暴行,成为一个体制的造反者时。我们到底要怎样对待他,才能称之为 justice in love,才能区分一场正义的审判和一桩可耻的谋杀。信仰法律,到底是信仰什么呢。对上海的法官或成都的一年级大学生来说,这追问都一样尖锐,一样难过。
2008-10-1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