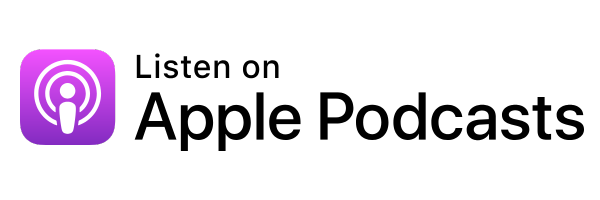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来说,最为至关重要的乃是人民应当受到法律的统治
——《1660年威斯敏斯特议会宣言》
国王应当不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律。
——柯克
对比“议行合一”和“分权制衡”这两种思路。会发现司法权在宪政制度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出于对孟德斯鸠式三权分立理论的不满,有人提出“统治权”与“司法权”的两分法,可能具有一种更非常鲜明的宪政主义色彩。因为它概括出宪政主义不同于民主主义的两个精髓,一是对一种支配性的公共权力(行政和立法)在整体上的质疑和制衡,二是对司法权捍卫原则、理性、在先价值和宪法权威的宪政功能的高度张扬。
在奠定了民主制和分权模式的前提下,美国宪政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司法权崛起的历程。《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将这句话拿来作为对统治权与司法权两分的一个本土思想诠释。用“祀与戎”的两分法,可以建立起一个诠释古典宪政主义到现代宪政主义的简洁模式。“戎”代表君王的统治权力,在远古主要是征伐,现代社会当然不止于此。而“祀”则代表一种具有超验背景的知识和道义传统。在远古,这个传统是由祭司或巫史来掌握的。所有的暴力操控在君王手中,祭司巫史们没有一枪一炮,一兵一卒。他们只有一张嘴,和嘴里面的话语权威。但君王的一切决策和重大纷争的裁判却要先咨询他们,也可能因他们的卜筮和预言而被否决。这种局面与宪政国家中最高法院执掌的违宪审查机制是颇为相似的。
假如说在民主制度下得到民意合法性支撑的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替代了自古以来属于“君王”的统治权。端坐高堂之上的5名或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其宪政角色就是现代宪政模式中的“大祭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意思,放在远古,可解释为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来自祭司代表的“道统”和君王代表的“政统”之间的均衡。放在某些宪政国家,则是最高法院代表的“司法权”对国会和总统代表的“统治权”的制约。
立法权和行政权至少有三个共同的、与司法权迥异的特征。其一,它们都是一种支配权,富于进攻性和主动性。意味着公共权力对个人和公共生活积极的改造、修正和冒犯。其二,它们在民主制下都具有直接的民意基础,这个基础赋予它们说服力和合法性,但也因此加剧了统治权的自负和危险。而宪政制度的本质是对唯意志论的反对,无论是一个人的意志还是多数人的意志。国家需要一个更高的裁决者,和一种知识与价值的传统,去制约本质上属于“君王”的无边意志。其三,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混合趋势在现代政治中越来越明显。一方面,议会把更多的立法权授权委托给了政府。另一方面,议会也以立法的方式频频干预和处分行政事务。这种立法的泛滥败坏了古典的法治传统。鉴于这种混杂,立法权和行政权几乎已经失去了本质上的差别,而沦为行使统治权的两种具体技术。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日益下降为“君王”权力的一种内部监督机制。
晚年的哈耶克曾对此深恶痛绝,提出一个三权变五权的方法。把立法权分解为一个更加消极无为的、元老院式的“纯粹立法议会”,和一个从事具体立法工作的议会。再把行政权分解为一个光说不练的“政府治理议会”,和一个跑腿的政府管理机构。单就立法权这一层而言,他的设想是想勾连英美两种体制,把美国最高法院的“祭司”功能搬到一个古典的英国上议院去。但这种模式无疑是对马歇尔大法官开创违宪审查制度以来的现代宪政主义的一个反动。在他想象中的“纯粹立法议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必将出现立宪政体中一个不可弥补的裂口。这也显出了“统治权”与“司法权”两分概念的意义。研究美国宪政史,可以看到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职能交换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统治权的本性使然。唯一的道路是近代以来英美立宪主义的历史道路,即一条司法权崛起,从而制衡统治权、约束民意可欲范围的“祭司”之路。
如果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一个宪政的基本模式。可以接续中国古典政治传统和英美的现代宪政制度,从中拉出一根本土资源的线索来。在观念的层面,我将中国的宪政主义政治哲学划分为“神权宪政主义”、“儒道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三个阶段。
通常认为中国古代是政教合一的,这不仅在制度上,也在观念上完全排除了“祭司”制约“君王”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祀”与“戎”这两种权威在古代中国大部分时期是分开的。周之前大致属于“神权宪政主义”,祭司和巫史代表了一种针对君主的知识与道义的霸权。君主没有彻底占据和颠覆过这种神圣性的话语权威。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文王困而演周易”为止。文王演《易》是中国政治史上政统与道统合一的象征性标志。从此世俗君主拿走了巫史阶层的话语特权,“祀与戎”开始合一,“天子”自己成为“圣人”。早期儒家的兴起也未能扭转这一模式,直到旬况,仍然主张“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但天子并未真正取得政教合一的地位。“尊君”和“罪君”的观念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学者张分田认为“尊君—罪君”范式,是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结构.所谓“君君臣臣”,就是要求“为君必君,为臣必臣”,否则就是天下乱之本也.而“天下有道”,“道高于君”,则是人们评判“为君不君”的超验正义。张分田认为,“道高于君”是罪君思想进一步的政治哲学化,贯穿中国历史,融合儒道法各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群体的政治信条和政治信仰”。君王被品分为两种,有道和无道。孔子从正面提出“以道事君”的教导,孟子进一步提出“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反面选择,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激进主张.而管仲甚至主张“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的积极的反抗,此种决绝的姿态,与自然法面对君王权柄的审视是相似的,与教皇格里高里七世和托马斯?阿奎那基于宗教权柄认为教会或人民有权废黜皇帝的观点,也惊人地相似。
秦政之后,董仲舒倡言天道打压君主,开创出一种复兴的儒道宪政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总纲是“屈君而伸天”.随后儒道法慢慢合流,再次将“祀与戎”分开,把“祭司”的权威从皇帝那里抢了回来。从此大约两千年,尽管皇帝自命为天子,亲自主持祭祀。但皇帝的权力并没在政治哲学上僭越于由儒生职业集团所把持的具有神圣性的“道统”之上。也从未有资格与当时某位大儒或风范大臣竞争最高的道义形象。“祭司”的精神权威存在于皇宫之外,“道高于君”始终是历代帝王无法超越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一道统直到20世纪的反复革命中再现了“文王演《易》”的旧事,中国史上第二次出现周文王式的“君师合一”,在台海两边分别庚续出“祀与戎”合流的现代意识形态政体,这才再被扭转。
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主流,一直包含着“道与势”、“祀与戎”的两分。“君师合一”才是偶然和非常态的,是对某种古典宪政主义努力的背叛。尽管笔者所谓的“儒道宪政主义”和远古的“神权宪政主义”一样,主要指一种非制度的话语权威的模型。并未落实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力,也未针对皇权形成过制度意义上的、能与英美宪政主义相提并论的分权制衡术。但不能说儒道传统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制衡皇权的观念力量,甚至也不能说儒道宪政主义就全然没有制度上的积累.
如在孟子那里,已有过以知识传统为凭籍反对君王干预司法的主张。后来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开创了后世礼法合一的路径,“春秋决狱”之于古典中国的意义,其实是堪与马歇尔法院一系列宪法判例之于美国宪政的意义相媲美的。它的主旨是“屈法以伸伦理”。以当代的目光看这是法律的泛伦理化,但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这恰恰是一种专业化,是凭借知识与价值传统制衡君王意志的杰出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孝”对抗“忠”。以私人价值对抗国家价值,以儒家伦理对抗君王的统治权。如“亲亲相隐”的原则,为近亲属豁免了作证和检举的国家义务,这显然是一个从国家的枪口下力争过来的自由传统,体现出对私人价值的珍惜.
“礼法合一”为儒生集团逐渐取得了一种超越在朝代更迭之上的“祭司”身份。两千年来,儒道两家的价值传统渗透到法律中,对君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构成过一些有效的制衡。如学者研究清朝的刑部案例,发现刑部经常反对皇帝本人对一些案件的处理意见.刑部官员们所凭籍的资源,正是“五伦定罪”的律法传统及其背后源远流长的“春秋决狱”的儒家司法精神。只是在英美宪政主义的制度成就对照下,这些制衡技术就显出它过分的脆弱和不可靠。
儒家传统基本上以家族而非以个人为价值本位,这与以“个人自由”为在先价值的宪政主义有天壤之别。但这不妨碍“君王与祭司”、“统治权与判断权”这一宪政主义的两分政体框架的成立,也不妨碍儒道宪政主义以私人关系对抗国家义务这一核心倾向的成立。对宪政化有着更大意义的正是这一基本模式。一个可贵的事实是,在中国古典政治传统中从未诞生出类似于欧陆哲学中的国家至上的主流观念。相反,这一传统中同样蕴涵着一种与现代宪政主义的方向具有一致性的观念张力,蕴涵着一种在世俗权力和君王意志面前所积累起的知识与德性的尊严。只不过这一知识和价值的传统本身,需要放下百年来的胸中块垒,在具有普适性的人类超验价值传统面前学会谦卑、顺服与更新。
转身观察英美宪政的教训。用“祀与戎”的模式看,可称为法治传统下的“司法宪政主义”.这在精神观念和政体结构上和本土的“神权宪政主义”和“儒道宪政主义”雏形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只在英美才最终养成了立宪的制度成就和更坚实的自由价值。因此对中国来说,宪政转型的历程就是法官集团继巫史集团和儒生集团之后,最终变迁为政治制度当中制约统治权的第三类“祭司”的历程。这三类“祭司”的共同点是除了一张嘴和一枝笔就一无所有。占卜、儒学和司法,分别是他们制约“君王”和对政治进行判断所凭籍的知识传统。司法宪政主义不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政治,它的核心特征是以理性制衡暴力,以价值制衡意志,或者说以“道”制衡“势”,以“祀”制衡“戎”。归根到底,是以一种手无寸铁的力量去约束国家暴力。司法对大众而言,事实上是一种寡头体制。司法权是消极的和阴柔的国家权力,就如一位女性。如果其它权力有骑士风度,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Ladies first”(女士优先)。
在英国宪政的发展史上,没有一个人群比普通法法官作出的贡献更大。英美的判例法和法官造法的传统,直接塑造和捍卫了共和政体,并不断打破中世纪的各种贸易垄断,发展出自由的契约关系,为资本主义奠定了稳定的法治基础。康芒斯指出,“在很早以前,习惯法法院的法官们已经明确的指出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任何人只要能使国家致富,也允许他发家致富。但是如果他单纯的从共同的财富中榨取私人的财富,那就是不许可的”.如1599年,高等法院宣布伦敦成衣商协会一项维持行业封锁的细则为非法,尽管这一行会规则得到了历代国王和历届议会的确认,但法院仍然宣称其“违反了习惯法,违反了人民的自由,违反了共和政体的精神”。在1615年另一件成衣行业的案件中,一个根据亨利七世的特许成立、并得到议会确认有权制定章程的成衣工人协会,依据自己的章程取消了一名成衣工人的从业资格。法院根据习惯法“不得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合法的行业”,否定了类似的市场准入的禁止,指出“这一切都是与习惯法和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
1608年,柯克法官在博纳姆案件中否定了允许医师行会惩戒医师的一项议会立法,此案是人类史上司法权凭借理性传统审查立法的开端,也被视为违宪审查制度的一个起点。柯克法官在判决中宣称:
在很多情况下习惯法可以约束议会的法案,有时并可判决其完全无效:因为当议会的法案违背公共利益和理智或不宜或不可能实行时,习惯法就可以抑制它,并宣告议会的法案无效.
柯克当时提出这一“祭司”权柄的正当性基础只是普通法传统,而不是立宪政体的框架。8年之后,他被英国国王詹姆斯免职,表明司法宪政主义“第一波”的失败。在美国建国初期,司法权同样是三权之中最弱的一维,被视为一种“既无钱又无剑”(汉弥尔顿)的权威。不比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的知识权威高出半分。这种以柔弱胜刚强的知识传统,最终成为美国宪政的阿基米德支点,摇身变为立宪政体中最高意义上的政治权威。现实途径就是对声望的积累,对权力的自我节制,和对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知识传统的反复依赖。一旦法官在现实中滥用违宪审查权,僭越立法权的权限。就将引发各界对司法制度的猜忌,并使公众失去对法律的信赖和尊重。19世纪末以来,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最终确立,与“司法克制原则”(doctrine of judicial self-restraint)这一法官们立志持守的品质与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在马歇尔法官作出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后,司法拥有宪政最高意义上的裁判权的理论曾一度受到质疑.1936年大法官斯通在一项判例中,提出了司法权在确认法律违宪性时,应受两项原则的约束:
其一,法院仅能审究制定法律法律的权限问题,而不能审查法律的内容是否睿智。
其二,行政部门及立法部门于违宪行使国家权力时,如应受司法的抑制,则对于法院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牵制,应是本院法官的自我抑制意识。至于诉请将不智的法律从法典中除去,则非可由法院为之。而因诉诸选票或循民主政府的程序为之。
斯通坚持唯有法官才是“宪法的最高解释者”这一宪政主义立场。唯一可以牵制司法权力的,是法官面对宪法和法治传统时的自我克制。司法权的自我克制与违宪审查制度是“主权者的自我约束”这一宪政主义硬币的两面。都是对在先价值和法治传统的承认和信服。
无论罗马法还是儒家教化,都曾在人类史上开创出一个以知识限制意志的传统。其实质就是以逻辑约束民意,以价值约束经验。尤其是罗马法的市民法,被称为“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在现代社会,法治及其学术传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因为崇尚建构理性的倾向和规范化、完美化的法典编纂传统,学术对民意的宰制体现得较为明显。法学家立法,是整个大陆法系耽于逻辑严密的理念世界和一个封闭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整体特征。法学家似乎拥有了某种口含天宪的代表权柄。转型国家如果沉湎在以这种立法的自负为蓝本的法典移植中,往往将给社会带来“法律的专制”(孟德斯鸠)和对一个自由的自生秩序的摧毁。其一,通过立法颠覆个人长期形成的合理预期.其二,通过立法将大量私人事务和民事、商事活动置于非法的境地。随之造成政府“选择性执法”的腐败空间.其三,私人根据一切未阐明的规则(unarticulated rule)形成的合理预期都不能得到保护,被排斥在法律化的个人自由的门外.
而普通法是一种尊重惯例的法治道路,尊重惯例的意思是捍卫每个人的合理预期。一个人的合理预期就是这个人的权利。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具体技术就是尊重惯例的法治观。所谓惯例“就是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去策划未来的那种常识的行动,而契约本身就是惯例,惯例的约束力量就在于对预期的保证”.过去发生的事或承诺将要发生的事,有权基于我们的预期而发生。使这一预期落空的一切人应当受到惩罚。在这种法律观下,除了邻居,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最可能被惩罚的人。法律的确定性,不在于法律本身是否成文,在于每个人在既定的法律秩序和正当的个人行为中所形成的那些预期是否具有确定性。从英国的柯克、布莱克斯通到美国的詹姆斯?C?卡特,显出一种与宪政主义相吻合的保守主义的法律立场。法律不是被制造的,而是被发现的。法律不是上对下的命令,“法律存在于人民的惯例中”,法律“是从公正的社会准则,或从产生这种准则的习惯和惯例中产生的规则”.支持和延续一种习惯不需要举证,否定一种习惯或事实需要举证。因为“普通法法官的主要关注点,必定是一项交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所可能合理形成的那些预期。意即当事人根据一不断展开的行动秩序所赖以为基础的一般性惯例而形成的那些预期”.这种法律观正是法律制度的确定性的保障.而成文意味着反复的成文,换言之“成文”几乎就是“修改”的同义词。因为崇尚成文法规的精确无误,甚至迫不及待的通过不断的立法调试去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残酷到不顾念一部分人在这种立法调试中因预期被颠覆而丧失利益的地步。在这种立法崇拜下,那种“尽可能允许个人根据几个世纪、数代人形成的一整套规则制订计划的”,由“民众自发采行,而由法官揭示出来的”法律的长期的确定性,被替代和遮蔽了。
在这样的普通法的立宪主义道路中,除了一件具体案件中坐在法官席上的那个人,还有谁更有资格在与当事人相关的一项法律和当事人的一项预期之间作裁判呢?法官的裁判高于立法者的意志,不是因为法官本人高于立法者,而是一个当事人的合理预期高于任何人的立法。因此在英美普通法传统中,限制民意和防止预期被颠覆的重心,就从法学家和立法者移到了法官,也从静态的立法学移到了司法的技艺理性(柯克)的积累。法官成为了共和政体下的祭司,和每个人的预期的捍卫者。因此麦基文将从法官们的判例发展出来的普通法法治,视为“中世纪宪政”的主要成就.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在完成笼罩整个世界的自负的立法工程后,多数唯理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者如霍布斯、奥斯丁等,并不强调甚至反对属于法官的知识传统。英美法恰好相反,认为“法官的使命是一种智识的使命”(哈耶克)。柯克更将司法视为“最高的理性”。普通法的经验主义特征在立法环节为民意留下足够的空间。技艺理性的积累又在司法环节为共和主义的精英立场创造出一个修复和看守机制,为法律制度和宪政制度的“自生演进秩序”提供了可能。
2016年9月14日
文章来源:王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