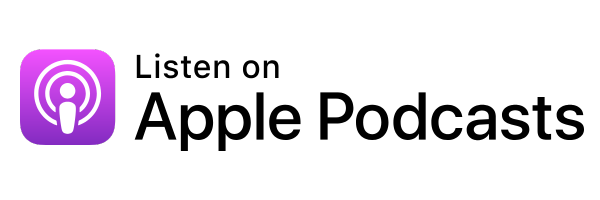在清教徒世界观的尽头,是一场最后审判。宇宙在根本上是一个法庭,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一个救赎与审判的关系。尽管这是有恩典、有怜悯,也有赦免的审判,但仍然是一场审判。简单地说基督教就是“来信耶稣真正好”,简单地说“神就是爱”。这并非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因为“神爱世人”的那个爱,不是我们理解的卿卿我我的爱,也不是父母为儿女死都愿意的那个爱。而是上帝在他的创造、救赎和审判这一永恒的旨意当中的爱。是上帝从他的永恒意志中发出的,定意如此、非如此不可的爱。也是上帝将他所创造的人带入与他的圣约当中的爱。“神就是爱”的爱,是牺牲的爱,更是立约的爱,是意志的爱,也是公义的爱。这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宇宙世界,即使没有十字架,上帝对人和万物的审判也是完全公义的。但上帝定意如此,他不在没有救赎的情形下施行审判,反过来,他也不在取消审判的情形下施行慈爱。
基督徒的审判观和他的国度观有关系。因为审判是主权的体现。谁对这个世界拥有主权,谁就有权力、也有责任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这几百年来最大的一个政治神话就是国家主权的观念。国家主权是一个谎言,国家主权是催眠术,不管它的外观设计是哪一种政体,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我们都在这一观念下成为国家的奴隶。它虚构了一个无罪的主权者,也虚构了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因而也彻底塑造了我们对审判和法律的看法。几百年来,我们没有被启蒙,而是被哲学家们拖入了更深的蒙昧当中。他们把“主权”这个概念擦得干干净净,擦得一尘不染,擦成一个形而上的偶像,好像这个世界不受罪的影响。但在基督徒看来,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上,没有神圣的和完整的主权,只有在政治上被人拜来拜去的偶像。如果宇宙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主权者,如果没有一场宇宙性的审判,能够将完全的爱和完全的公义成全在一起。那么大地上就没有审判,人也不能冒充自己是法官。
基督信仰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审判观,就是救赎与审判一定有关系。就是赦免与惩戒一定有关系。什么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刑罚观,那就是,大地上一种没有赦免制度的刑罚制度,一定是不公义的。你们能够同意吗?为什么1949年后的中国刑罚制度是不公义的。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已经谈过了,另一个理由,就是1949年以后,我们杀人杀得性起,革命革得坚决,就把任何赦免制度都废除了。但你看整部人类史,包括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赦免制度。整个刑罚制度,尤其是死刑制度,一定是和赦免制度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刑事赦免非常多,因为古人还是敬天畏命的,古人的脑袋里还没有冒出“国家主权”这种政治偶像。所以在他们那个世界的场景里面,皇帝通常不是用杀人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相反,皇帝是通过赦免来获得合法性的。为什么中国追求了一百年的现代化,到1949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哲学和政治哲学,反而变成了只能用杀人来论证合法性呢?
你看古代的皇帝在登基、大婚、立储或其他重要时刻,都会大赦天下。中国人把唐朝当作盛世,唐朝的刑事赦免是历史上最多的。你要和谐社会吗?对不起,“严打”是反和谐社会的,赦免才是社会和谐的道路。1949年后,共产党只用过一次政治性的赦免,他刚取得政权之后,赦免了一批战犯,要显示出政权交接时的稳定。但在普通刑事制度里面,没有了。其实这在人类几千年的刑罚史和政治史上,是一个耻辱。我们在座每一个法律人,到今天为止,都担当着这个耻辱。
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救赎。如果你了解基督信仰的这个审判观,你会重新来反思我们对人间法律的理解,好像法律就是强制力之下的主权者的意志和命令?我们有两个最粗暴的观念,可惜迄今为止法学院里还在大规模的教育学生,一个是把法律看为主权者的意志,这是唯意志论的法律观。一个是把法律看作强制力的体现。这是一种唯暴力论的和残忍的法律观。这是两种与刚才我讲的国家主义崇拜,或对国家的偶像崇拜有直接联系的法律观。它也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价值乃至与文化的关系,“法不容情”成为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律是什么,不过变成了我们头脑里那个残缺的世界图景的一个片断。彻底的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其实是最形而上学的。当然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把法律人的良心一笔勾销,好让我们晚上能够睡得香。某种法律观的经济价值,就是可以节省很多安眠药。你看电影里面,监狱头都有牧师,警察局都有心理医生。其实法院、检察院和律师楼,是最应该聘请心理医生的了,当然有牧师更好。
于是我谈到最后一部分,我理解和坚持的宪政主义,是以裁判权为中心的宪政体制。我不用“审判权”,以免与在具体的司法制度当中被定义的那个“审判”概念联系太紧了。我用“裁判权”。谈这个理论之前,我先讲在《圣经》里,最能体现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中的审判和国度的看法的,就是基督耶稣在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所受的审判。这是地上的政权按照当时最先进的罗马法,对一位自称上帝独生儿子的人的审判。无论你是否相信耶稣是基督,这都是人类史上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一次审判。耶稣在彼拉多讯问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对话。这是耶稣对世俗国家及其审判权的一个根本的理解。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首先,彼拉多直接向耶稣宣告一个世俗国家的审判权柄。耶稣的回答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没有否认地上君王的审判权,他事实上接受这一场审判。而且他还遵循罗马法的诉讼原则,来为自己抗辩。耶稣拒绝回答“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一提问,暗示指控方应该自己举证。第二,耶稣指出这个世界同时是天父的世界,地上的国度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国度。因此也有一个更高的审判者。
至于这场更高的审判与彼拉多的审判之间的关系,耶稣指出了三点。第一,地上的审判权柄,是从“天上”赐下的。人间没有主权,人间的一切权柄来自上帝的授权、委托和默许。第二,即使得到授权,地上的审判也不是独立的,依旧处在那更高的权柄之下。耶稣暗示彼拉多,这一场审判的结果,最终是掌握在耶和华神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他或凯撒的手中。这也是耶稣顺服地上审判权的原因。就像罗马书第13章说,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基督顺服彼拉多,不是因为惧怕彼拉多的权柄,而是因为顺服神的主权和旨意,刚才说神的主权,这是基督徒世界图景的核心。
所以耶稣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话很有意思,如果实体上的审判权柄在彼拉多手中,如果地上的裁判就是最终意义上的裁判。那么在原告、被告和法官的三角关系中,法官的罪显然要比出卖和控告耶稣的人的罪更大。因为他要为一个错误的判决背负最高和最后的责任。但耶稣这句话指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法庭,另外一场审判,和另外一个三角关系。在那个三角关系中,在实体和最高意义上为判决负责的,乃是上帝。彼拉多并不处在法官的那个位置上。耶稣说,在对我的审判中,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第一男主角。也幸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在真正的审判者那里,出卖者和控告者的罪,反而比你的罪还要大。
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的背后其实有两重审判。第一重是看得见的那个审判,犹太人是原告,耶稣是被告,犹太人控告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和弥赛亚。彼拉多是法官,他三次公开宣称按照罗马法,耶稣的罪名不能成立。但他仍然违心的屈从于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将一个按世俗法律的标准无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看不见的审判,上帝容许撒旦站在检察官的位置上,就像他曾经控告约伯一样。人类是被告,上帝是审判者。撒旦以谎言诱惑人犯罪,随后控告人的全然败坏,指控他们背弃了神与人的约,没有一个人能行出神所喜悦的公义和良善。这个指控是成立的,上帝按他的公义作出判决,罪的代价就是死。
这时你就看见唯在审判中才显明出来的“神爱世人”。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基督就是上帝。他道成肉身,和人类一样活在肉身之中,同样经历了撒旦的试探,但却保持了全然的公义和圣洁。上帝决意在基督里受难,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替那被判死刑的人类付出刑罚的代价。因为耶稣是真正的人,他能够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真实的死亡。又因为耶稣是基督,是圣洁的神。所以一个义人的血可以满足公义的要求,将一切不义之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在这个看不见的审判中,基督是那一只献祭的替罪羊。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相信上帝借着他在审判中的拯救,在拯救中的审判。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
耶稣回答彼拉多的那句话,显得很温柔,也很坚决。他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死,不是因为你的这场审判,是因为你看不见的那一场审判。不是因为你有权柄刑罚我,是因为天父的旨意,要“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来拯救罪人。只要一个人以信心来回应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为他流血的人。
其实还有第三重审判,耶稣在受审之前对他的门徒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是指着基督的复活说的。基督以他的死为世人赎罪,勾销了撒旦的指控。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为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带来了盼望。撒旦就是辖制这个世界的力量,圣经中称他是“这世界的王”。所以第三重的审判,就是在末日对撒旦和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撒旦和我们的公安很像的。他先设一个套,向你买毒品,等你把毒品拿来了,就抓你,然后告你贩卖毒品。为什么那个买的人就没有罪呢?因为他是撒旦,你还没有堕落之前,他早就堕落了。但如果有人像基督那样替这个卖毒品的去上十字架,那么最后上被告席的,其实就是这个警察。
我只是一个比喻。基督在末日与天父一道施行审判。但他在自己尚未被捕受审之前,就把自己复活之后的,那个永恒当中的终极审判,告诉了门徒。“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接下来我们看洛克的政府论。洛克是一个清教徒,他的国家学说建立在这种整全的圣经世界观之上。洛克国家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契约论,而是裁判权。他把裁判权分为世俗国家的裁判权,和末世论意义上的上帝的裁判权。洛克说,什么是自然状态呢?所谓自然状态不是一个没有行政权的状态,而是一种缺乏裁判权的状态。每个人在一切冲突中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高大法官。我们知道英美普通法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则,“一个人不能做他自己的法官”。这不是一个被简单化了的司法原则,而是国家的政治哲学当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所以洛克说,这样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只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判决结果“在最后的审判日,向万民的最高审判者承担责任”。用我们的术语说,这就叫“眼睛看不见的公平”了。因此国家的本质,就是裁判权的建立。契约论的目的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裁判权,而不是建立人对自己的“主权”。这是他的契约论与卢梭契约论最大的不同。对比洛克的国家理论,和耶稣对彼拉多的回答,你就能看出当洛克论述世俗国家的权柄时,他的那个世界的图景和耶稣是相似的。而你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也可以看出卢梭眼里的那个世界的图景,和本丢·彼拉多又是多么的雷同。
主要是英美的基督徒们,在这个图景中去思考政府,就产生出我所理解的宪政主义。我所信奉的宪政主义,就是英美清教徒式的宪政主义,而不是欧陆的。如果没有英美这一枝,欧陆的极权主义倾向很难得到一个校正的机会。你就能看到二战的历史意义了。如果我说,要是没有二战,今天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有多可怕。你会觉得这话耸人听闻吗。我真是这样认为的。
从卢梭到康德到黑尔格和马克思,他们带出来的国家学说,是以立法权为核心的一种政体。裁判权如果不是一种妨碍,也是一种附庸。而清教徒的世界观带出来的国家学说,是以裁判权为核心的政体。立法权的背后是“主权”的神话,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国家观,好像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去实现善的目标。而后者是一种消极的国家观,裁判权的意思是抑制罪的扩展,而不是达成善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政教分离,宗教的功能是引导我们延展公共生活中的善,而政治的功能是在公共生活中抑制人类的恶。如果你认为国家有实现善的能力,有真理的教化功能,我就会说你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一个国家崇拜的迷信者。不管你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如何,你的立场在本质上就是政教合一。
一个以裁判权为中心的政体,是信奉超验价值的,而不是信奉“国家主权”的。是一个相信程序正义,而不是霸占实体正义的政体。但一些经验主义的学者说,我不相信什么超验价值,我只相信程序正义。这个立场实在是自相矛盾。如果你没有对超验价值的信奉,程序正义就变成皇帝的新衣了。法官相信自己只是坐在一个程序性的位置上,就像基督告诫彼拉多的那样,你不是坐在一个实质性的位置上。这是出于对那个更高的实体价值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信心指向上帝的主权和护理。仿照伯尔曼的话说,“程序正义除非被信仰,否则就是一个谎言”。
然后你来理解司法,在一个以裁判权为中心的,向着更高的国度和价值敞开的政体里面,司法首先不是一套技术手段,司法权也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权力平行的一种权柄。虽然我们很可怜,连平行都做不到。在清教徒的那个整全的世界观中看司法,司法权(裁判权)就是国家的本质。所以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的时代,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亲自为王。他们的领袖被称为“士师”,中文译本用了《周礼》中的一个职官名来翻译,意思就是审判官。更早的时候,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选立长老,也是为了裁判民事纠纷。但基督教神学中所讲的“民事”,是包括刑事在内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道德或“道德律”,涉及的则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要为洛克的国家理论找一个最贴切的实证,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形成了。以色列是典型的从裁判权开始形成国家的,他们在有君王之前,先有裁判者,按着上帝的律法在国民中进行审判。如旧约《申命记》中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当他们对上帝的律法不耐烦的时候,才吵吵嚷嚷的出现了君王。这个过程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里,如果要找第二个最接近的例子呢,那就是英国了。虽然裁判权并不像在以色列那样,是先于王权出现的。但在英国,王权的确立和裁判权的确立及普通法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同时的过程。所以在英国,法治传统也和君王的传统几乎一样长。
这种宪政主义,就是通过司法,以更高的律法来审视和限制国家。他的潜台词,就是在国家之上,还有更美好的国度。国家不过是一个器皿,而不是一个偶像。而一切专制主义,却把国家看作世界图景的中心。所以你观察司法权在一个国家政法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国家被偶像化的程度。司法权的地位越低,国家崇拜的程度越强。低到中国目前这个水平,国家就是法西斯,低到一个公安部长居然比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力还大,低到公安局长当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当副书记。有人说中国繁荣昌盛了,但你从这个指标看,今天的中国已堕落到人类政治史和法治史上的一个最低点。我实在想不出更低的类型,难道让派出所去管大法官?中国有希望啊,有希望的意思就是筑底筑得差不多了,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痞了。所以大家要有信心等着翻梢。
我忍不住讲个故事。不久前到法国,去他们的司法部。法国司法部和中国有许多培训项目。我说了两个建议,第一,少培训一点法官,多培训一点律师。今天的大律师才是民主中国的大法官。第二,少跟最高法院合作,他们不管用。希拉克很快下台了。维护法国的利益要把眼光放长点,不要老跟中南海打交道,多些对民间力量的关注,尤其是跟律师界的合作。法国人就很惊讶,他们说你们的最高大法官很牛啊。肖扬访问法国,那个排场把他们都镇住了。第一,肖扬是“国家领导人”待遇,副总理级别,有礼炮的。第二,他们说在凡尔赛广场上,好多中国游客认出他,都抢着和他照相。司法部官员满脸羡慕,好像在说咱们的法官做梦都梦不到这么风光。我说,在法国最风光的是不是电影明星啊,在中国也是,最风光的那都是演员。最高大法官在中国,是仅次于人大委员长的国家二级演员。罗干你们知道吧,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肖扬一个中央委员在他面前算什么呢。但罗干出访却没有他风光。因为现在常委太多,哪有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的帽子给他呢。他出去就没有礼炮了,连警车开道都是中国使馆花钱租的。公安部长出去就更没级别了,不但没有炮仗,人家连报纸都懒得报道。但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肖扬至少排在二三十位,在他后面老远呢,平常要见上一面恐怕都难,看人家心情好不好。我说,你们的司法部长虽然没有炮仗,但不至于排二三十位吧,宪法委员会主席可是排第5位的。
司法权的政治地位贬到这个份上,这样的政体不叫法西斯,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法西斯了。这样的国家不叫警察国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才叫警察国家。
最后,思考以裁判权为中心的宪政体制在中国的可能性,我就谈自己对近期中国政体变迁的两点观察。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和全国人大,已经开始争夺未来政体转型之后的制度角色了。以及在这个争夺中,最高法院已经不堪一击。我把今日的政体,称为“一个恶汉三个帮”。恶汉是谁就不说了,是谁谁自己站起来。三个帮呢,一个人大,一个政府,一个法院。这三个就是宪政模式中的三权。共产党在技术上,必须借助这三权。尤其在文革之后,有一个逐步借助三权的的趋势,不得不如此。因为他的合法法面临崩溃。尤其在64之后和全面市场化之后,借助三权的趋势更加明显了。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一般把这个趋势叫法治化。中国人说话都很文雅,什么叫法治化,意思就是“三权起来,干掉党权”。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他拐弯抹角想说的,就是让我来代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吧。就像一个恶汉,养了三条狗,三根绳子都牵在自己手上,一根都不想放。咬人的时候,就让三条狗相互配合,分工合作。
但最近十几年的社会进步,就是人大、政府和法院,这三家村都在茁壮成长。当然政府膨胀得最快,但政府的膨胀在观念上没有正当性。人们普遍的希望,是通过立法权的崛起,或者司法权的崛起,两头夹击,去限制政府权力,然后三权协作,或者等待地方和民间的势力,或者参与逼宫,最终在某个时候干掉党权。这就是未来政体转型的一个大概。这个大概一定会发生。但人大和法院,一旦党权衰落了,谁才是“老大”呢?这才是中国未来政体转型中最关键的问题。
一种模式,就是法院的裁判权在三权分立中占据一个消极的但却最高的位置,成为一切纠纷的最终裁判者。“最高”法院的意思,不是说在所有法院里他是最高的,而是说他在整个社会是最高的。这是我推崇的美国的宪政模式。国家不要赶走了共产党,又走到另一条“人民主权”的偶像崇拜的路上去。这也是国内自由主义学者比较主流的一种倾向,我想这也是“法政系”的主流理想。另一种模式呢,就是立法权最大,人大开始来牵这个狗绳子,一个至高无上的议会,成为国家主义的继承人。这是很多体制内学者比较主流的一种倾向,如蔡定剑他们,拼命想把人大变成另一个共产党。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转型如果走到“人民主权”的落实即某种议会至上主义去,也是很可怕的事。我坚持的宪政主义,只能是以裁判权为中心的,我叫做“司法宪政主义”。这与诸位的价值理想和职业立场也是一致的。
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最高法院也在努力,他一直通过司法解释的技术,很小心的抢夺着法治化过程中的主导权,也积累未来从政治图景中的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的政治合道性的资源。人大一个法律出来,也许200条,我一个司法解释出来,可能有400条。现在管不管用不要紧,共产党垮的那天管用就行了。法治化需要技术和权威的积累,总不能到了那一天才哗哗地出来吧。甚至有时一个法律在人大那里长期窝出不来,最高法院干脆就自己制定司法解释,替人大立法了。
你可以说政体改革还没有开始,但最近几年也有两个微妙的政体变迁的征兆。多数学者和评论家都比较忽略,或者故意不说。
第一个是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国家主席”条款的修订。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评论。只是给国家主席的职权加了6个字,“其他国事活动”。原先宪法中的国家主席,在理论上我们叫“虚位元首”。他的职权就清清楚楚的列了那么几条,如根据人大决定宣布战争,和平,紧急状态,接受外国使节等。没有任何兜底的补充或一般性的定义。这是一个完全的“虚君”,理论上比英国女王虚得更彻底。因为女王还有许多习惯法上的权力,只是一直克制着没有行使过罢了。但04年修宪开了一个口子,“其他国事活动”。这是什么意思啊,宪法上的“虚位元首”是不是要走向“实位元首”?这么严重的政体变革,瞒天过海就改成了。所有学者都装着不知道。以前共产党的党魁,是不兼任国家主席的。那时的“国家主席”的确比较虚。但江泽民以后,因为权威不够,怕镇不住台面,就似乎形成这十几年来兼任国家主席的惯例。那么现在胡锦涛是“国家主席”,你怎么评价他的地位?从宪法体制上讲,他是虚位元首。但他是党的总书记,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实位元首。党国合一的好处,就是虚虚实实,你想看清楚,就看得你流鼻血。就像武侠小说一样,把内功注入到一个家伙身上去。共产党快要死了,就赶快把几十年的功力,注入到一个穴位里去。这个穴位就是“国家主席”。各地的党委书记纷纷兼人大主任,也是一个意思。共产党不是没有考虑后事。凡是专制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会提前为自己修坟墓。共产党对政体变迁的想法是什么呢,至少胡锦涛的想法和台湾一样,想走的是法国的“超级总统制”模式。就是不被嵌入在三权分立当中的总统制,而是高踞于三权之上的总统制。这种总统制通常叫“半总统制”,但到最后一定是超级总统制。
这种政体的特点,就是不但不放弃一个完整的“人民主权”的国家崇拜,而且舍不得放弃一个完整的象征。我曾请教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和曾作过宪法委员会主席的巴丹戴尔。为什么法国不能接受对议会的“违宪审查”?为什么不把宪法委员会对法案的事先审查,改成可以针对法律的、可由公民提起的事后审查?巴丹戴尔自己提过这样的议案,但没通过。结果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法国人还不能接受对“人民主权”的任何割裂和对完整性的否定。“超级总统制”也是一样,法国人的国家崇拜是近代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希望像美国那样,找不到一个家伙,可以站在那里代表整个国家,成为国家主权的品牌代言人。胡锦涛的修宪,表明他的B计划可能就是走法国的路,这是我个人坚决反对的道路。
第二个,是人大隐忍很多年,终于对最高法院动手了。它借着全社会呼唤违宪审查的舆论,给了最高法院正面的回击。05年12月20日,大人常委会通过了一个《司法解释审查备案工作程序规定》,其中要求“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和审查”。最高法院显然没有一点反弹力,所以06年紧接着又出台了《监督法》,正式确立了人大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权。换句话说,明早起来一旦没有了政治局,这个社会的最高裁判权已被议会抢到手中了。人大公开宣布三权之中我最大。等老头子死了,家产都是我的。这件事比前一桩更严重,因为换成别的国家,这就足以导致宪法危机了。人大的意思,就是要求重新洗牌,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期权,老头子还没死呢。人大的意思,不是否定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而已,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司法权的性质。他的意思跟共产党一样,就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叫做独立的司法权的玩意。
宪政和法治社会最起码的一点,就是承认法院的裁判权,法院有权在一个具体的法律争议中去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并有权判断什么是法律争议。这是司法权的题中之义,不承认这个就等于不承认司法权。你可能说,目前的宪法的确规定全国人大有宪法解释权啊。就算这样,但除非人大自己亲自去审理案件,否则他的一切立法(包括宪法)和一切解释(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只是一个文本而已。一个法律文本仍然要在具体案件中,由法院去解释和适用。而不是说,法院的解释又要拿回人大去重新解释。那人大的新的解释文本,是不是又要在具体场合的适用中被法院再次解释呢?
结果就是,只要你建立“法院”,你就必须承认,法院的意思,就是这个社会最高的和最后的裁判者。这就是民主与宪政的差别。否则你干脆不要法院好了,你自己作法官好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就是这么干的,议会自己做法官。共产党也是这么干的,政治局常委其实就是最高大法官。多可怕的前景啊,就算我们等到共产党完蛋了,我们也可能退回到一个比古希腊还不如的政体中去。所以我说,扶持全国人大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就是扶持下一个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就是反法治的;并且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就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
我主张的宪政主义,是“司法宪政主义”。如果议会成为最高的裁判者,裁判权就不再建立在人类的信仰和价值传统之上,而成了一件数人头的事情。民意只能成为民意代表的合法性来源,民意不能成为裁判权本身的来源。否则对基督徒来说,这就是对上帝的公开叛乱。对法律人来说,这就是造法治传统的反。对自由主义来说,这就是革自由主义的命。你也不能把英国的宪政模式简单理解为议会至上。你要放回它的整个政体图景当中去评价,君主制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法治的传统。除了英国,谁能同时有这三个制衡议会主权的力量啊。宪政体制之所以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因为他是以价值来约束权力,以一个手无寸铁的机构,来约束身怀利器的机构。裁判权是一个堕落世界中的上帝律法和人类价值的守护者。这个制度上消极的守护者只能是法院,不能是议会。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你知道一些国家,在大法官椅子背后刻着“十诫”。但你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议会的椅子背后刻着“十诫”呢?问:为什么“十诫”总是被刻在法院里,从来不刻在议会里?
一种答案是,因为刻在议会里,议员们就要失业了。另一种答案是,因为一个法官以他信奉的律法为神,而一个议会则以他自己为神。
遗憾地是,今天中国的法官们看起来,几乎是这个社会中最不像价值和信仰的守护者的那种人。那么律师的制度、角色和社会使命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律师是未来宪政体制和“司法宪政主义”的重要力量。今天的一党专制,未来的议会主权,都是“司法宪政主义”的敌人。一个以裁判权为中心的宪政中国,要靠这一代的“法政系”去担当。我最后有三个建议给大家,第一,把司法权放在整个宪政框架中去观察,把宪政体制放在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当中去观看。第二,也把你的律师角色,把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都放在同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当中去理解。第三,既然“十诫”还没有被刻在中国的法庭上,那么,先在你律师事务所的墙上挂上“十诫”吧!
我讲得太多。谢谢大家。
(根据2006年11月在上海“青年律师沙龙”上的讲座整理修订,不具名地感谢几位邀请者和组织者。)
推荐四本关于基督徒世界观的书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世界观的历史》,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评介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观和世界观概念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演变的译著。
荷兰十九世纪的政治家、新教改革宗神学家凯波尔的著作。他的《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完整的阐释了改革宗神学的世界观,在国内2005年出版的《加尔文传》一书附录中有收录。
美国当代政治家、神学家寇尔森的《世界观的故事》,台湾校园出版社2006年1月。这本书生动描述了基督信仰不只是一个私人化的救赎,而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寇尔森详细阐述了这种圣经世界观与世俗文化的关系。
陈庆真的《世界观的交锋》,台湾校园书房2002年。这大概是华人世界中第一本仔细论述圣经世界观与人本主义、及科学主义世界观之差异与冲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