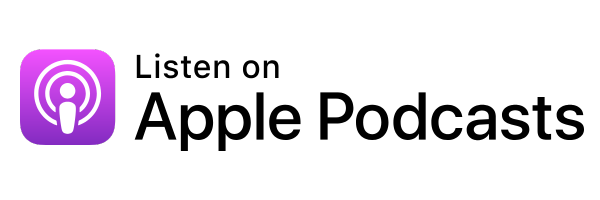1.联邦主义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炎武《日知录》
在共和主义传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自由传统不可能与一个庞大的国家兼容。这是一种直观的认识,假如同意个人权利的在先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同意每个人的自主是一个阿基米得支点。那么国家越大就意味着权力的中枢离我们越远,显然也就越不容易被控制。在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杠杆越长国家越有力量,个人自由就越发的微不足道和缺乏保障。在那些庞大的君主制帝国,个人与国家之间往往是一个漫长的杠杆和几乎空白的社会空间,也就是张东荪先生所谓中国自古以来的“两橛政治”
这条通往国家权力中枢的线条可以拉得更长。几乎所有古典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思想家,从孟德斯鸠、洛克、休谟以及贡斯当、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等人,到当代的哈耶克和布坎南,都主张某种形式的联邦主义,把联邦政体视为宪政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孟德斯鸠这样论述地域大小对政体的影响:
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大小应该适中;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如果狭小将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广大,人们会对来自遥远而又迟缓的惩罚无所畏惧,因此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拥有专制的权力。从自然特质来看,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开明的君主治理,而大帝国只能由一个专制君王来维持。因此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
孟德斯鸠进而认为扩大疆域而能维持原有政体的唯一办法,就是联邦392。联邦共和国既由小共和国组成,在国内它便享有每个共和国良好政治的幸福。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联合的力量,它又具有大帝国所有的优点。
按博克海默的观点,“联邦制是两个或多个分享权力的政府对同一地理区域及其人口行使权力的体制”394。
从美国建立第一个联邦制的立宪政体,到苏联解体的二百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土面积在 100 万平方公里之上的民主国家,全都实行联邦主义。所有国土面积在 300 万平方公里之上的国家,都实行联邦主义。中国是目前唯一的例外395。尽管数量上联邦主义国家全世界只有 20 多个,仅占国家总数的十分之一,但联邦国家占去了全世界面积的的二分之一和人口的三分之一。
2.纵向分权
联邦主义也是分权学说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权分立是一种横向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针对的是全权主义;联邦主义则是一种纵向的分权(division of powers),它瓦解的是某种中央集权体制。有学者直接将联邦主义与
纵向的地方分权看为同义词397。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封建制度的契约色彩曾经为一种联邦主义的分权模式提供了想象空间和历史的路径依赖。后来随着商业城市的发达,城市共和体之间的分立逐步替代了封建领主之间的分立,但一种契约化的传统得到了延续。
如最古老的联邦主义国家瑞士,在 13 世纪就出现了许多城市自治体之间的联盟。1291 年 8 月 1 日,当时的三个州签订了永久同盟条约,这个盟约成为瑞士联邦的宪章,这一天成为瑞士的建国纪念日。不过那时的瑞士联邦只是今天称之为的邦联。
中国从秦朝废封建开始,就终结了任何一种中央与地方进行契约化分权的可能性,从此以一种科层制的官僚体系(郡县制)取而代之,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体模式。但事实上即使是集权程度最高的行政体制,也不可能将权力的触角如臂使指的伸到每个遥远的角落,因此行政权在事实上的纵向分配是不可避免的。老百姓常说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权力是自上而下、长途跋涉赶来的,那么一个漫长得不可想象的代理人链条也不可避免。在中央集权制下,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官员,反而在合法性来源上距离我们最远。因为皇帝在逻辑上是第一个直接的统治者,而那个距个人最近的官员却距皇帝最远。他和某个管制对象的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是这样的:他是有权进行统治的皇帝的代理人的代理人的代理人的代理人……
这个事实带来两个重要的效果。
第一,来自权力中枢的意志到了最基层,几乎没有任何方法能保证它不被扭曲。几乎没有辅助性的制度可以担保层层代理之后,末端代理人的行为还能完全符合被代理人的利益和动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像一个摆钟,只可能在极端的专制和极端的割据之间反复。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割据与分裂恰恰是中央集权体制衍生出的产物。其一,越是缺乏横向分权的集权体制,越容易产生割据。三权分立通常被理解为横向上的分权,但它同样也会产生纵向上的制衡效果。因为每一级地方政权的三权分立,会瓦解地方政权在政治上的自足性。尤其是一个拥有独立权威的完整的司法体制的存在,使一个实行分权原则的地方政权在一种法治的统治方式下,不可能具备自足的权能和正当性。
其二,越是加强纵向上的行政集权,就越有机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诸侯化398。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理论上可以干预地方的一切政务,但事实上行政权将不可避免的批发给各级代理人。中央政权又必须保持行政权在理论上的一种完整性,因此这种分散必然缺乏明确的纵向分权,其边界只好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实力比较和政策走向而随意收缩或膨胀。一旦地方的实力强盛起来,中央就缺乏控制诸侯的更为稳定和安全的制度设计。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没有一个实行国有产权制度的政府能解决国有产权体系的代理人问题。御史、观察使、巡抚、总督、监军、政委、督察员、稽查员,各种技术层出不穷。只要不从中央集权转向多中心的自治和分权,都只能治一时之标而不能医本。
第二,越是贴近个人的权力,反而越是专断和蛮横。因为权力没有和权力的管制对象建立起一种和平的政治渊源,即地方的民主与共和。本土的暴力机构没有和本土的人民达成契约化的谅解,官员手中的权力自上而下,与辖区内的公民无关。这样的政权本质上是一种“外来政权”是一种殖民政权,带来权力的膨胀和冷漠。因此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即便最高权力实现了合法性的民主化转型,不再是皇帝、独裁者而是一个民选领袖。地方的政治仍然是非民主的。地方一天不能自由选举,对地方而言政治就是专制的。
清初,大儒顾炎武回顾明朝和历史上愈演愈烈的专制倾向,曾提出一个打破两千年秦制的救弊办法,就是回归分封制下的地方自治,“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通过分权于下,实现多头的地方政体对上级、对中枢的制衡,并能够有效伸张地方的个别利益。顾炎武的纵向分权方案,明显带有现代联邦主义的色彩。因为这已不是简单的对行政权的纵向分配,而是对地方政权某种独立地位的承认。这就接近了联邦主义双重主权、两级政府和复合共和的本质特征。
判断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自治或放权改革的区别。从价值上,看是否承认一种多元主义的和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框架;从技术上看,地方仅享有独立的行政权,甚至有一个从属性的地方议会(如英国的北爱尔兰)是不够的,关键应看地方是否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和财政权。联邦主义并不反对中央政府的统一财政和强制性的转移支付,包括横向的和纵向的。汉弥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着重阐述过转移支付对于联邦的重要性。在德国的《基本法》中,也规定了富裕州必须向欠发达州进行横向财政补贴的义务。但联邦主义国家的各州政府,都保留了在一个独立范围内征收赋税和使用赋税的自主权力。国家权力中枢有没有垄断征用私人财产的赋税大权,是判断联邦制国家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任何对集权制的有效分权最终都要落在人事与财政两方面。联邦主义国家的地方议会,享有条块划分下的立法权(A 的立法归联邦,B 的立法归地方)而不仅是级别划分下的立法权(A 和 B 的立法归中央,A1 和 B1 的立法归地方,但不能与 A 和 B的立法相违背),这样的地方议会才是独立而非从属的。地方的独立赋税,削弱了权力中枢无限的财政能力;地方的独立选举,使议会能够真正控制地方主要官员的任免,化解了来自权力中枢的人事威胁。中枢国家权力因此不能再简单的依靠命令和武装去指挥全国,必须放下身段在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之中,去发展宪政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技术。法国中央集权体制的改革非常典型,中央政府逐步放弃对地方的人事与财政的指令,尝试更多的通过司法权这一更高的权威去实现对地方的宪政约束。
尤其是在联邦制中,司法权居于显赫的位置。联邦主义的存在,不依靠司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恰恰相反,因为联邦主义在地方与中枢之间实行了立法和行政的纵向分权,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法治化的新支点和稳定秩序的源泉。在一种契约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也需要一个高于它们的中立者来做裁判。因此在立宪国家,司法领域是唯一一个不被民意割裂的权力堡垒。除了美国、墨西哥和巴西外,大多数联邦制国家都只有一套统一的司法体系399。前三个国家尽管有联邦与地方两套平行的司法体系,但这与两套政府、两套立法体系的意义并不一样。尽管存在着司法管辖权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基本上不是条块的划分而只是层次的划分。最高法院凭借宪法的最高权威凌驾于一切法院之上,终审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以州权的名义或地方的民意去对抗。在统一的宪法权威及其司法标准上,没有州权可言。这一点使最高法院具有类似于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所具有的不容置喙的地位。联邦主义把这种地位交给了在本质上具有否定性和消极性的司法权。于是在联邦主义的观念下,所谓统一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和宪政的统一,在技术上则表现为司法权和司法标准的统一。所谓爱国也是对这一统一的法治与宪政秩序的热爱,而不是对一个统一的政府系统的热爱。
3.乡镇精神
托克维尔当年访问美国时曾惊讶于它的乡镇自治。他感叹说: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也没有。
乡镇任何国家都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群体生活的集合。但绝大多数国家的乡镇因为有国家垂直权力的侵犯,无法发展为一个自治的“乡镇共和体”。在北美 13个殖民地,因为英国总督的统治较弱,也因为美国乡镇的移民特征清除了一种宗族式的精英统治方式,使乡镇的崛起天然地具有某种个体结盟的色彩。在此背景下美国乡镇自治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哈耶克所称的“自生秩序”的契约化扩展过程。托克维尔高度激赏这种乡镇精神,认其是美国联邦民主制的基础。事实上,一个个乡镇共和体的直接民主实践,也是美国“州权”观念形成的关键。乡镇自治蕴含了联邦主义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对过于遥远的权力的不放心。如果民主与共和是值得追求的,身边的民主和父老乡亲之间的“共和”,显然比亿万人之间的共和更重要,更踏实、更首先。
早先在古代英格兰的基督教教区中,也存在类似的乡镇(教区)自治。这也是美国清教徒乡镇精神的一个源头。从个人的自主,到群体的自治,再到多元共和体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个脉络显示了联邦主义的共和主义底色。联邦主义的共和是一种“复合的共和”,也就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多元的共和。其一,联邦是一种共有与共治的政体,这和单一制的共和国家是相同的。其二,构成联邦的每一级地方政权,仍然是一个共有与共治的共和体。这种复合是对共和主义的一种深化,是真正贯彻到底的共和制。所以联邦主义最准确的称呼是“复合的共和制”,而不能简单称为民主制。
简单的民主“在本质上是非共和性质的400”,一个实行了单一民主原则的大国,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全体一亿人之间是“民主”的,但将任何一个千万、百万之巨的地方人群剥离出来看,则可能缺乏民主。我们只看到垂直的权力系统如何像吊车一样运作,看不到一个千万人的庞大群体有任何“共和”之迹象。实行单一民主原则,意味着政治由一个简单多数决定。而建立在地方自治之上的联邦主义则是对民主原则和简单多数原则的一种制衡和过滤。联邦制意味着“多重的多数原则”,联邦一级实行多数原则,每个地方共和体内部也都实行多数原则。双重或多重的主权就意味着双重或多重的多数,这就最大限度避免了在政治上形成绝对多数的局面,也避免了某种一竿子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权力正当性来源。因为在多重多数下达成的公共决策,已不再体现任何人、任何群体的简单意志。
4.单一制与联邦制
通常在政体理论上,习惯将联邦制与单一制相提并论。但站在立宪主义的视角下看,并不存在地方权力绝对从属于中枢的所谓单一制的立宪政体。绝对意义上的地方的“分公司”模式401是和宪政民主制度对立的,只可能存在于独裁的体制下。
以中国为例,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帝制时代,其政体才是绝对意义上的单一制。即地方一切长官由中枢任命和委派,地方一切权力的正当性都来自于中央。在中国,这是以“春秋大一统”为观念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欧洲,这种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源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的绝对君主制的遗产。但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全世界任何一个共和制国家都存在某种形式的地方议会。这些议会即使是从属性的,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法国;地方议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单一制政体理念的一种重要修正。孙文在辛亥时期一度提倡地方自治和建立美式联邦的思路。从民国 9到民国 20 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与地方自治思潮一度风云交汇,对中国两千年君主制下根深蒂固的垂直政体传统曾产生了相当的瓦解作用。当时这一运动甚至影响了中共在其“二大”时提出了“自由联邦制原则”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革命思路。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大钊在论民主制度的《平民主义》一书里,也认为联邦主义是民主的必然衍生。直到《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共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的构想都一直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潮,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体目标。直到 1956 年,周恩来在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解释性报告中,仍在“民主集中制”的思路下倡导地方民主,并针对“中央与地方分权”、“集权与分权”等问题作了阐释。周恩来显然对权力集中制就等于风险集中制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主张“多多发扬地方民主,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 402。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对地方的放权改革,加上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实施。地方权力完全从属和源自于中央的授予,这样一种绝对的单一制的政体理念事实上已被破碎,而逐渐被一种高度混合的政体模式所修正。全世上也找不到一个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不是以某种程度的地方共和体的自治为基础的。因为在立宪政体下,“代议制民主”是比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区分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在国内的传统政治学框架中,“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体划分,长期以来是在未引入宪政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形成的。因此造成了对两者差别不恰当的夸大。在宪政国家中,也有单一制与联邦制之别,但并不如通常理解中那样南辕北辙。尤其在二战以后,单一制的宪政国家几乎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联邦化色彩的地方自治改革。1968 年,被视为最标准的单一制国家的意大利颁布《州制实施法》,这既可以被看作一种联邦主义运动,也可以看作单一制国家同样能够引入地方高度分权的因素403。地方共和体的自治,使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划分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也使联邦主义不再被误解为一种造成分裂和不稳定的政体。因为民意是从地方逐层过滤的,一个建立在民意表决之上的宪政体制,必然要以地方权力的某种自洽性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起源。
5.两院制
两院制是个有关自由的问题,它是自由政府的未来,而单院制导致独裁统治。——托克维尔
上述这句话是托克维尔对两院制的赞美,和边沁的立场刚好相反。作为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边沁对权力制衡所体现的自由价值似乎不太感兴趣,他直接而苛刻的认为,两院制的“第二院是不需要的,无用的,比无用更糟糕的”。一个持相同观点的神父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如果第二院和第一院意见一致,第二院是无用的,如果不一致,第二院是糟糕的”。
这两种看法似乎都过于偏激。据统计,到 1996 年,全球有 36 个稳定的民主政体,里面单一制的民主政体有 27 个。这 27 个国家刚好一半实行两院制,一半实行单院制,事实证明都运行良好。但联邦主义和两院制显然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并为两院制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在统计研究的 9 个联邦制国家中,全都采用两院制的议会模式404。
两院制通常被看作是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是一种重要的“多重的多数”。它使民意在最高层分流,得到再一次过滤。这使任何改变现状或大刀阔斧的立法冲动都变得困难重重。无论在英国式的古典议会还是在现代联邦主义国家,所谓两院都并非是完全平行的两院,往往是由一个精英化的上院和一个相对平民化的下院构成。下院一般是主要的和日常的立法机构,在议会内阁制下通常也是制衡和选择政府的主要场所。上院比较接近于哈耶克设想中的“纯粹立法议会”,它以一种精英化的立场和权限对下院进行制衡,具有明显的共和主义色彩。当然两院之间的制衡也是相互的。在一些设立两院的单一制国家,两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上、下之分,如意大利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享有几乎完全平等的立法权和宪法地位,政府也必须同时得到两院多数的支持。
两院制在历史上历经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主要是混合政体思想的体现,由一个贵族院和一个平民院构成,各自代表社会上层和中下层的阶级利益。这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并列。在中世纪则以英国的两院制最为典型。在英国,两院的模式是君民共治、混合主权的一个反映。清末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曾这样描述两院制405:
泰西列国设有上下两院。上院以国之宗亲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
后来戊戌变法中关于议会的讨论,一种通行的观点即由“国家爵命之官”组成上院,而由“绅民公选之员”组成下院406。
当共和制取代君主立宪后,两院制的去留成为一个焦点。混合政体和阶级平衡不再构成一个说服力,法国革命中人们认为在一个所有公民都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立法机构中实行权力平衡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法国人以 849 票对 89 票,建立了一院制的议会407。数年之后,美国总统亚当斯眺望欧洲,将法国革命的灾难归结于他们对一院制的“致命的”的选择。在美国制宪之前,除了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坚持一院制,其它多数州都仍然实行两院制。这也许出自一种良好的惯性,尽管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不再,但只要人们仍然并将永远分属在不同的利益和意见群体中,两院制带来的立法权的均衡和对简单民意的拒绝就依然是重要的。
美国确立联邦政体,为两院制的传统重新找到了理由,恢复了活力。新的理由即州权与人权、州意与民意的平衡。既然联邦建立在地方共和体的契约之上,每一地方共和体都应该具有平等的缔约地位,这种平等权并得到一种政治盟约传统的支持。但州权的平等却与人人平等的民主理念产生了冲突。每个人的平等、每平方公里的平等还是每一个州的平等?解决这种冲突的唯一办法是继续借助两院制,让每个州的民意代表组成参议院,而让每一同等规模人群的民意代表组成众议院。众议院显然更符合一种直观的民主理念,因此将日常的立法权交给整个联邦的民意代表,而将一种审视性的和更消极的立法地位交给各州的民意代表。这样两院制完整的体现出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走向:以共和主义的传统去制约政治上的多数(民主)。
在最近欧盟立宪的道路上,可以看到一种替代两院制的新方法。欧洲人在一个单独的议会中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双重多数原则。一方面按照成员国平等的原则,投票需要成员国的多数通过。另一方面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又要求这些投赞成票的成员国的人口,必须占到欧盟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前一个是邦联的原则,后一个是联邦的原则。用一院制议会的一次性投票来混合这两个原则,体现出欧盟作为一个新型的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特点。但这种混合仍然只是表面上的,人口原则只是计票时的一个附带因素,不能真正构成另一种利益博弈的方向,最多只具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意义。因此这种替代方案对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宪政转型而言,并不具有范式的启发意义。
“一阴一阳谓之道”,政治的折衷与妥协,是从古希腊混合政体思想到宪政主义、联邦主义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分权原则和财政问题,始终是这一政治折衷的主要兴奋点。宪政主义者热爱的是一种俯身向世的经验主义的政治智识,而不是一昧沉迷在逻辑世界中的抽象的兴奋。
注释:
392 两段引文分别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P124 和 P131,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393 戴维·J·博登哈默《联邦制与民主》,宪政论衡网站,www.xianzheng9.com。
394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P35,北京大学 2000 年。
年。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185.
原理》,P218—22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7 月。
发。
399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P23,北京大学 2000 年。
年。
401 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从分公司到子公司”。
402 周恩来《关于体制问题》,参见《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P302—307。
40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对联邦主义和社会整合的看法》,《宪政新论》,P16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04阿克曼《新分权》,秋风译,未刊稿。
405 见《郑观应集》上,P103,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406张学仁、陈宁生主编《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P12,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07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P82,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摘自《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
2006 年初于成都大学。
2011 年 10 月完成修订。
——摘自《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