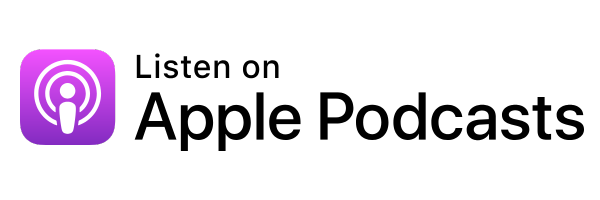王:谢谢杨教授,谢谢大家。电脑前的朋友应该有我认识的,也有很多不认识的。故雨新知,以这种方式连在一起。中国家庭教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蛮大的题目。我就从我们教会不久前发布的《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谈起。教会在中国的公开化,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认信的公开化,就是一个信仰告白的运动。向全社会公开宣告,我们到底信什么。因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是家庭教会”,“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认同政教分立的立场”,这几点就一直写在秋雨之福教会的章程里,所以最近的这个文件,是对此的一个神学性的重申。
这个文件的思路,大概分两个部分,前一个是神学性的,就是从上帝的主权,独一上帝的创造,祂的护理和祂的拯救,从救赎历史来认识教会历史,来认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神学性的阐释,涉及到对神的主权的认识,和对上帝救恩的认识。从这里去看教会论,即教会是什么?然后再来讨论政教关系,及个人的良心自由问题。
第二个部分,涉及中国的现实。就是讨论三自运动的兴起,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还有“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官方主导的政策,以及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或说十字架神学的传统。在这个部分,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一直到今天,它所有的困境,挣扎,艰难,还有它的全部信仰实践,所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
这是大白话,如果改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描绘这个“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的难题,那就是,到底你的宗教观决定了你的政治观,还是你的政治观决定了你的宗教观?也就是说,有一个皇帝,或者今天虽不叫皇帝,叫做有一个党,总之在你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笼罩一切的最高统治者,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几乎可以决定你生活中一切大小事情,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与神的关系?
还是反过来,其实有一位上帝,是祂创造了这个世界,祂以无尽的爱来拯救你,祂掌管你的身体和灵魂,祂也掌管宇宙和历史中的一切事情,但祂的掌管是隐形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唯独透过信仰才能知道和经历这一点。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跟那个皇帝的关系?
所以,“家庭教会”这几个字,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在1949年后,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全面进入了20世纪人类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和一种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彻底的无神论政权的治下。这一特定的历史处境,即使放在2000年教会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20世纪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经历了类似局面,但差不多都慢慢过去,尘埃落定了,而且曾进入这一历史潮流的俄罗斯和东欧,他们之前已拥有基督教的生活与文化传统。而对中国来讲,这一处境直到今天,第一,它没有结束,而且尚未出现结束的征兆。第二,它的文化背景里几乎没有基督教的文化根基。它是最强烈的东方传统的专制主义,加上最强烈的从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自己讲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一种政治文化与实践。而这种政治处境,给全体中国人,包括基督教会,都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压力。每个人都要回答,你到底怎么活?对基督徒的良心来讲,就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这是兹事体大的,一个生与死的抉择。
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其他群体包括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讲,都不是那么尖锐。重要,但没有重要到生死攸关的地步。因为像余华说的,“活着”本身,或者说血缘的延续,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偶像。就像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被杀的人对杀他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老婆又怀孕了”。你杀了我又怎么样呢,我老婆又怀孕了。所以,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对一个57年的右派来讲,他虽然存留了一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自由主义的思想走,对他来讲,并没有惨烈到一个地步。这是一个令他内心煎熬的问题,但还不足以令他毁家弃子,背弃君王。
所以,一个很核心的对“家庭教会”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和我们的良心的关系。唯有“家庭教会”(包括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中国历史上,带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转变。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不是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决定的。而是反过来,我们对国家的看法,是由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所决定的。
神权与政权: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2)
杨:你们教会的这个立场表达是很清晰的。我想既然叫家庭教会,我们应该追溯家庭教会的来源,而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圣经时代。但我想在中国的特殊处境下,家庭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发展有一些什么不同阶段?因为今天在线的和在场的,很多不一定熟悉家庭教会产生的历史背景。你们为什么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怎么来的?能不能先简单谈一下这个缘起。
王:这个缘起呢,可以用49年做一个划界。在共产党入城夺权的前夕,48到49年,当时不同宗派的教会,召集了好几次应急会议。有一部分教会是乐观的,觉得共产党夺权后,应该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有一部分教会,特别是当时在华的长老会有几位宣教士,尤其是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牧师,他是美南长老会的。他们非常清晰地看见了共产主义的实质。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党是公开宣称不相信上帝的。但除了这一点,这一批极少数的宣教士也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实质。当然,很多人也对当时苏俄的现实和历史有所了解,所以,对中共夺权的恐慌和反对,其实在教会中是比较普遍的。包括本土化的教会,如上海的聚会处,甚至举行祷告会,祈求上帝拦阻共产党渡过长江。但另一方面,因为共产党宣扬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笑蜀主编的那本《历史的先声》,收录了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大量反独裁、要民主的文章,也蛊惑了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吴耀宗这一批青年会的现代派信徒。因此,教会中也有一大批人,是欢迎、期待共产党进城的。
因此,从48年到49年,在全国几个不同地方,尤其是在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中,譬如我所在的四川,就先后在万县和重庆,后来又在黄山,召开了几次基督教界应急会议,思量应怎么办?很多人提出各种策略和方式,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聚会,无论处境有可能变得多么糟。这时候,教会的确已经把自己未来的处境,和初代教会的处境与道路作为类比了。第二,于是,这些应急会议所,大不了我们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打散了,回到家里聚会,到野外去聚会,甚至找山洞聚会,因为初代教会就是这么干的。在罗马城的下面,有很广大的墓陵和通道系统,当时的教会就去“地下”聚会。于是,毕范宇牧师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转入农村、建立家庭教会”的方案。仿照使徒行传第7章,把教会的中心从城市转往乡村。因为在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中心一直都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因此教会说,我们要做好预备,从城市转往乡村,从会堂转向家庭,甚至预备在野外寻找地方聚会。
所以,实际上,在1949年,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已经在预备撤出中国,他们给中国教会预备的方案,就是化整为零,建立“家庭教会”。但从48年到49年,这些大宗派教会已经开始有所酝酿,甚至有些地方的教会,已开始推动建立家庭小组,就是为转向家庭和转向农村作准备。
反而,本土的大多数独立教会,直到共产党进城后,也还压根没有想过这种可能。如北京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1950年初,有次去天津一个教会讲道,在天津一个公园门口,看到一副标语,写着“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他心里就想,共产党还是很开明,应该守信用的,应该会尊重基本的信仰自由,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凶狠。
所以直到50年初,王明道还觉得未来蛮有希望,他认为局势不至于糟透。其实,大部分独立教会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也有民族主义情怀,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西方宣教士主导教会,所以这一批经过了本土化、本色化运动的独立教会,普遍认为自己和“西方帝国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显然,这一批基要派传道人在“通达时务”(旧约中对各支派族长的要求)方面,远远不及西方宣教士们。他们两袖清风,自认为无论面对西方教会,还是面对共产党,都是敬而远之,保持最低状态的关系,就可以了。但他们却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特征,以及意识形态与基督信仰之间生死攸关的大争战,存着中国人的侥幸的智慧,几乎没有什么深入认识。所以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所信的主耶稣,才是人家眼里的“境外反华势力”。
所以,在1950年,周恩来接见所谓“中国基督教代表团”的十几个人,其实都是他们钦点的。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研究,其中也许还包括了少数几位地下党员。1949年前,吴耀宗在武汉,就和周恩来秘密会面过。而共产党钦点的这十几个人,当时在教内的地位、名声都很低,包括吴耀宗本人,当时只是基督教青年会内的一个部长。因为有影响的大宗派的牧师,和本土独立教会的奋兴布道家们,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于是,周恩来安排这个代表团,去全国各地巡回考察,所到之处,均由当地党政要员接待,扶持他们在教内的地位。
从周恩来与吴耀宗等人的三次见面后,凯撒和希律,还有祭司和犹大,都成了朋友。共产党紧锣密鼓地推行“三自反帝爱国运动”。一部分教会猛然惊醒,因为49年之前就有所预备,于是,一批人开始脱离原来的教会系统,私下进行聚会。而像基督徒会堂这样的独立教会,就更加凸显出独立的姿态,像王明道,几乎和政府、三自、大宗派等教内外一切组织,都划清了界限。他以自己个人的属灵影响力对外发言,因为他创立了一份著名的《灵食季刊》。三自运动开始后,他的订户反而直线上升。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当时少数几个拥有微信公众号的传道人。
这样,“家庭教会”首先作为一个现象,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但我并不把1950年“三自爱国反帝运动”的爆发,作为中国家庭教会正式诞生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有选择自由的,你不这样做,也还不至于杀头,也不会坐牢,不会在政治上被判死刑,打成反革命。那时候,只是一部分人开始基于他的信仰,意识到,我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了。这条路的代价将有多大?连决心走这条路的人里面,也没有人知道。
于是,我是把王明道在1955年6月,发表了最重要的那篇文章——他在那一年发表了三篇文章(有点像马丁路德在1520年发表了三篇檄文,在某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认为,那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始),其中,最重要的那篇是《我们是为了信仰》——视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
这篇长文,可以说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最杰出的护教辞。在第一世纪,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涌现出许多护教士,也写了不少的护教辞。王明道发表的这篇文章,很清晰的,既有神学上的意味,也有政治上的意味。他说,“我们相信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而且“没有一句是帝国主义的毒素和毒草”。那么,前半句是神学上的认信,我信圣经的权威和无误,这是我的生命信仰之根。而后半句就是回应政治上的挑战。教会现在被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一个侵略工具,而我坚持说,不,它与帝国主义无关。我的信仰,不可能在共产党进城之后,变得和共产党进城之前不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等于拒绝政治可以影响你的宗教。在王明道那里,政治不能影响宗教,是一个宗教的立场,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然而,只要你不承认政治有改变你的信仰的能力,你的信仰立场在共产党眼里,就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立场了。所以我说,它是同时有神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含义。这就是“护教辞”的意义。先有护教辞,才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这一双重立场的产物,即当一个古老的认信在特定的政治历史处境下被宣告出来后,教会就必须、也只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因此,王明道直接宣称,那些参加“三自运动”的人是“不信派”。因为他们既看不见这一点,也不相信这一点。看不见是因为不相信。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人,只看得见君王的刀剑和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一部分教会和传道人在政治上迎合和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毒素”这样一个罪名,被加在基督的教会身上,不,甚至是被加在基督本人身上时,他们也就在神学上背弃了教会最古老、最基本的认信。
其实,耶稣在罗马帝国之下被钉十字架,祂所承受的罪名,也是类似的。翻译成1950年代的话,就叫“反革命罪”。翻译成今天的话,就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不过,王明道的这篇檄文发表之后,共产党是想尽了办法,反复争取他。因为王明道是中国自立教会中一个重要的领袖,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借助他在教会的影响力。当这种努力失败后,或者说,当政府对这种努力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就转变态度,决定逮捕王明道。这时,和王明道站在一起,还是和吴耀宗站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和王明道在一起的,是曾被杀的羔羊。和吴耀宗站在一起的,是罗马帝国。这时,是秘密聚会、脱离三自;还是签名自保,加入三自,就成了一个信仰的生死测试。因此,我认为,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及政府对他们夫妇的逮捕,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